剧情介绍
本片是苏联纪录片导演,“电影眼”理论的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代表作。电影主要拍摄于乌克兰的敖德萨市,摄像师是维尔托夫的哥哥米凯尔•卡夫曼(Mikhail Kaufman)。影片主要分观众入席、城市黎明、人民的工作与休息、体育运动和艺术实践几部分,通过刻画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呈现苏维埃新社会中的一个理想城市。摄影师米凯尔•卡夫曼在拍摄的同时也出现在电影画面中,首创了“自我暴露”的电影形式。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性突破意义的纪录片中,维尔托夫首次使用了二次曝光、快进、慢动作、画面定格、跳跃剪辑、画面分割等前卫剪辑手法,并采用了仰角、特写、推拉镜头等新颖的拍摄手法,并制作了一段定格动画。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励志少年罪恶之路校门外石狮之超能记者五个叔叔一个妈第一季龙少爷粤语邀请函2020英国的七个时代龙老大凉山传奇泰坦 第三季小飞侠闺蜜离婚指南第三季为子搬迁美国出口奔腾年代第一季小双侠女人本色2007爱的遗产愤怒的伦理学猎犬山第一季不要变成西瓜啊!主任!仙猫传
长篇影评
1 ) 电影眼、都市生产与影像生产
观众入座,电影即将放映,而被放映的正是《持摄像机的人》的主体部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视觉旅行,我们将随着镜头穿越一个城市、一个日夜,捕捉城市生产和再生产的每个悸动,并把它们编织成一支辉煌的都市交响曲。而我们也同时意识到,正是摄像机的发明才使这种视觉旅行成为了可能。
《持摄像机的人》标志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所栖息的都市突然具有了生命,而这种自在自为的生命通过一系列极为先锋的电影影像技巧呈现在我们眼前:升格摄影、降格摄影、双重暴光、快速蒙太奇等等。和大洋彼岸的好莱坞同仁不同,吉加•维尔托夫并不把这些刚刚发明的特技看作是迷惑眼球的伎俩;对于这位电影革命者来说,所有这些特技都是表征城市的必要手段。正如他在那热情洋溢的视觉革命檄文中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电影眼”(kino-eye)的诞生。不过,和寻常的理解不同,“电影眼”并非人体肉眼的单向衍生;它是肉体与机械的弥合,肉眼与工业视觉的杂生。只有在“电影眼”乃至在电影这一新兴媒介中,维尔托夫才找到了机械与劳动力之间的辩证平衡。
数十年之后,先锋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在他的《录像带谋杀案》等片中重复/倒置了这一辩证关系。那些从人类肉体中增生出来的机械或者机械的情欲化成为了后现代电影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意象,而与此相关的则是柯南伯格所着迷的后工业时代地下都城。这些欲望横流、阴郁冰冷的都市显然和维尔托夫在《持摄像机的人》中所建构的那个理想都城不同:那是莫斯科、敖德萨和基普的结合体,通过繁复的蒙太奇手法变幻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之城。
但是,和柯南伯格如出一辙的是维尔托夫把身体的生产—城市的生产—视觉影像的生产置于了同一个平面。在这一天的都市生产生活中,不同生产领域的工具与结构都通过蒙太奇手法被诗意地连接在了一起:比如说,火车轮、纺织轮和胶片滚轮,运输、生活资料生产与影像生产都在“电影眼”中呈现出相似的运作方式,并强调了普遍性生产方式的可能性。
如果说,对柯南伯格电影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解读是,资产阶级个人在媒介时代中遭遇了最终的疏离,并通过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而得到了唯一救赎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持摄像机的人》刚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题:大工业生产并不必然产生疏离和物化,不同生产领域、不同工种之间都可以提炼出新的抽象形式。《持摄像机的人》以视觉的形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对话。在后者中,纺织工业成为了整个物质生产历史的缩影,而在前者中,纺织工业中的滚轮和轴轮则成为了影像动力学的起点,从工业作坊到现代电影大工业,从衣物生产到视觉景观的生产,每一个生产门类都被历史化地连接在一起,现代都市以其意象上的相似性被巧妙地构想在了一起。
于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被发展成为蒙太奇理论。通过把社会各个部门的工业活动理性化、流程化和标准化(奇怪的是,和之后的文化批判者所设想的不同,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所暗含的并非剥削与日常生活的贫瘠,而是一种莫名的诗意),蒙太奇超越了电影技术本身的含义,而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它既是碎片,又把碎片有组织地连接在一起;这既是现代生活的本质,又是现代社会与电影叙事体系生产意义的方式。
当一种理想、理性的现代都市生活在《持摄像机的人》中被实现时,我们不能忘记的便是,只有在“电影眼”的关照下,这一切才能成为可能;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个仿佛多此一举的开场:对于维尔托夫的“洞穴人”来说,电影从来不是娱乐的幻影,而是教育和启迪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方式。当维尔托夫说“电影眼”是“一种影像记录形式,它不仅解构那些肉眼所能看见的世界,也解构那个无法看见的世界”时,我们总是能从与他同时代的本雅明那里找到回应:“我们的酒店与都市街道,我们的办公室与起居室,我们的火车站与工厂,所有这些都仿佛把我们毫无希望地囚禁了。然后,电影来了,它以十分之一秒的速度、以炸弹那般的威力把这个监狱炸得粉碎,于是,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废墟之中自由自在地畅游。特写让空间扩大;慢动作让时间延长。随着摄像机的升高和降低,电影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无意识的视觉世界,就像心理分析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无意识的欲望世界。”于是,在维尔托夫所想象的城邦中,电影以救赎者的身份降临了,社会的表层被光束穿透,被掩盖的社会关系在晦明之中更为清澈;当来自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公民在电影院中聚集,启迪的时刻就此来临。
2 ) film of life
Without any actors or sets, Vertov turned his camera to life reality itself. He captured objects in emotional qualities, inter-cut shots of people without awareness, and flashed quickly over structures. Camera quickly sliding over the surface of Soviet cities, I felt it could freeze any moment into film, expose any details onto the screen.
While watching this film, I felt myself like Vertov’s pair of eyes sensitive to any outside changes without any words. Along with his camera rolling, my eyes kept watching out. Underneath, there indeed wa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Vertov and me. We kept arguing beyond the experiences of this film: the meaning each shot convey, the state of human being, the essence of life etc. And those motion pictures reflecting on Vertoc’s life philosophy gave me a general impression of what an industrial city is like and how its citizens lived there during 1920s.
Furthermore, instead of fully use of words, Vertov communicated his life philosophy with audiences by pure cinematic language. In my opinion,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his visual ideas of time and space illustration. For instant, ordinary people could barely see if there is any combination between a scene of sleeping woman, a scene of cameraman, and a scene of running train. But Vertov successfully combined three scenes together with some sense of poetry. Such as, in the morning, the train was setting up from the station, but the sleeping woman felt too tired to get up for 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 cameraman started to set up his camera. Then, the train kept running on its track, the woman still struggled to wake up. And the cameraman set his camera on the track and waited train’s coming. While the train looked like going crack up cameraman’s body, the woman was suddenly awake from nightmare. Seemingly, she saw the cameraman being cracked by train in her dream.
This is really a good example, which we could much learn about how Vertov used the changing space to illustrate time, and how he brought up the idea of making this surreal montage. I believe, learning how to illustrate time and space well is a most significant thing of making a film, specially on those films of universal themes.
On a more technical note, I felt Vertov much like to shoot objects from unusual angles and made them metaphors for other life forms in this movie. For example, a street in the morning, running machines, and quick walking people without expression, such images quickly sliding over the surface of modern Soviet life, were frequently seen in this film. After hiding himself behind the camera, Vertov traveled over time and space, located anywhere to capture what he believed is reality: the film playing on the screen is our real life. Actors playing inside the film are ourselves.
3 ) 翻译 | 吉加·维尔托夫论《持摄影机的人》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电影传单FilmBooklets
文/吉加·维尔托夫 Dziga Vertov
译/MapleSaki
相较于先前电影眼睛派的作品,《持摄影机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耗费了更大的工作量。观察下更多的地点和拍摄时复杂的组织技术性操作可以为此做出解释。蒙太奇实验需要非同寻常的尝试。这些实验持续地进行着。
《持摄影机的人》是直白的,创造性的。它旗帜鲜明地反对电影发行商“陈词滥调,越多越好”(the more clichés,the better)的标语。这种标语令我们这些电影工作人员哪怕精疲力尽,也不会去想片刻休息。我们必须促使发行商,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尊重,把他们的标语晾在一边。《持摄影机的人》需要的是最具创造性的展示。
在哈尔科夫,我曾被问道:“为什么喜好那些跳动字幕的你,却突然带给我们《持摄影机的人》——这部没有任何文字和字幕的电影?”我的回应是,“不,我从未表示过自己喜欢任何字幕——那都是某些评论家编造的。”
的确,为进行坚决地净化电影语言的斗争,为使电影语言完全独立于戏剧和文学语言,电影眼睛派摒弃了制片厂、演员、布景和剧本。于是,在《世界的六分之一》(One-Sixth of the World)里,字幕游离在图像之外,与其隔绝,并对位地建构出一个文字-无线电的主题。
“在《第十一年》(The Eleventh Year)里,几乎没有留给字幕的空间(字幕图像的播出方式则进一步体现了它们不重要的地位),所以就算删去字幕也不会对电影的力量有任何干扰。”——《电影前线》1928年第二刊(Kinofront no.2 1928)
“一个真正电影-客体中的字幕,在其具体分量和实践意义上讲,就好比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货币时,对《雅典的泰门》关于黄金的引用。(《第十一年》的字幕便是如此)当这些字幕大部分都恰巧是确切的引述时,它们便可代表一本书籍在布局过程中的文本。”——《电影前线》1928年第二刊(Kinofront no.2 1928)
因此,《持摄影机的人》里字幕的完全缺席并不出乎意料,反而早在先前所有电影眼睛派的实验中都有所准备。

《持摄影机的人》不仅是一次实践成果的表现,也是一种银幕上的理论显现。这便是为什么在哈尔科夫和基辅就这部电影的公共辩论中,各方艺术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争执发生在好几个层面。一些人说《持摄影机的人》是一场视觉音乐的实验,一场视觉音乐会。另一些人则视这部电影为蒙太奇的高等数学。还有一些人则宣称这不是“原本的生活”,而是以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生活,等等。
事实上,这部电影只是其所记录在胶片上的现实的总和,如果你想的话,也可认为其不仅是总和,而可以是乘积,一种基于现实的“高等数学”。每件物品和每项要素都是独立的小文件。它们相互关联,所以一方面,电影将只由片段间的联系构成,片段联系同时也与视觉联系相吻合。另一方面,这些联系将不再需要字幕。于是,所有联系的总和便最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场复杂的实验是成功的,它被各抒己见的大多数同志们所认可。首先,它将我们从文学和戏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才得以见证百分之百的电影。其次,它用被摄影机(电影眼睛)所记录的“生活”来猛烈地反对被不完美的人眼所看到的“生活”。
选自 Kino Eye :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
4 ) (ZZ)维尔托夫飞翔的电影眼睛(陈岸瑛)
发表于《艺术家茶座》第1辑,2004年3月
一战后最令欧洲知识分子激动和兴奋的事情,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建立。那个时候,对先锋艺术持敌意态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没有最后确立,刚刚成立的新政府对艺术家的实验抱着比较宽容的态度,一大批先锋诗人、画家、建筑师和摄影师先后在政府的文化部门中担任要职。就电影方面而言,以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为代表的苏联导演,为世界带来了一股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新风。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年)演出人数达万人之多,这部片子按照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剧院”所创造的表现“群众哑剧”的方法,使人民群众成为这部“实况重现”的历史剧的主人。维尔托夫更是善于用摄影机来捕捉劳动和生活中的普通人,让他们生动自然的表情和姿态不受干扰地重现在银幕上。苏联的这些先锋电影,和西方以电影明星为中心的摄影棚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他的论文中,曾对苏联电影的这一做法极表羡慕,他说,“我们在俄罗斯电影中看到的一些演员,都不是我们意义上的演员,他们自己在扮演自己,并首先是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扮演自己。”1
维尔托夫(Dziga Vertov,1896-1954),原名Denis Arkadievich Kaufman,1896年2月2日生于一个俄属波兰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维尔托夫有两个弟弟,大的叫米哈伊?考夫曼(Mikhail Kaufman),从小热衷于摄影,后跟从维尔托夫拍摄纪录片;小的叫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曾参与法国先锋派电影运动,后成为美国著名导演艾里亚?卡赞和西德尼?吕美特的总摄影师。维尔托夫早年在圣彼得堡求学,学习医学和心理学,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追随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人。1916年至1917年间,维尔托夫建立了一个“声音实验室”,试验声音的各种蒙太奇效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给自己起了迭加?维尔托夫这个笔名。Dziga和Vertov这两个词都含有旋转的意思,Dziga Vertov这个笔名预示了维尔托夫日后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的电影生涯。十月革命后,维尔托夫加入了莫斯科的电影委员会,并当上了新闻片“电影周刊”(Kino-Nedelia)的编辑。在担任编辑期间,维尔托夫不仅加深了对电影的认识,而且还从堆积如山的素材中剪出两部文献纪录片,《革命周年纪念》(1919年)和《内战史》(1921年)。在这里,维尔托夫遇上了一位热心的剪辑员斯维洛娃(Yelizaveta Svilova),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日后成了他忠诚的妻子和帮手。
1922年战乱平息后,西方的故事片大批出现在苏联的电影海报上,维尔托夫对这些虚构的电影很是反感,觉得它们是生活廉价的替代品,和宗教一样都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这时,维尔托夫开始以“三人委员会”(troika)为名义发表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电影的躯体已经被习惯的剧毒麻醉了。我们需要机会在这垂死的机体上做一次实验,以寻找解毒的良方”2。维尔托夫的三人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电影小组,其成员是维尔托夫,他的妻子斯维洛娃,他的弟弟米哈伊?考夫曼。1922年5月,三人小组创办了一份《电影真理报》(Kino-Pravda),这是一种按月发行的新闻电影,间或也出产一两部具有正片长度的纪录片,它们由火车送往各地放映。“电影真理报”这个名字来自于列宁1912年创办的《真理报》(Pravda),它宣示了维尔托夫这样一个电影理念:无产阶级电影必须以真实为基础。
《电影真理报》的确做到了真实,它来自民众又归于民众,它源于生活但并不“高于”生活:
“莫斯科附近的巴甫洛夫村。一场电影。小小的放映厅内挤满了村民和来自附近工厂的工人。没有音乐伴奏的默片《电影真理报》正在放映,可以听到放映机的噪音。银幕上一列火车疾驰而过,一个小女孩出现了,并笔直向摄影机走来。突然观众中传出一声尖叫,一名妇女向银幕上的女孩奔去,她流着泪,伸出双臂叫着女孩的名字。但是小女孩消失了,银幕上火车再一次驰过。放映厅的灯亮了,那名妇女已晕倒,被人们抬了出去。‘怎么回事?’一名工人通讯员问。观众回答说:‘这是电影眼睛。他们拍电影的时候,女孩还活着,不久后,她生病死了。冲向银幕的妇女是她的母亲。’” 3
《电影真理报》的放映一直持续到1925年。在这三年里面,三人小组在一个老鼠成群的地下室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维尔托夫的妻子负责剪辑,弟弟米哈伊负责摄影,维尔托夫自己担任总指挥。米哈伊是个摄影狂,从早到晚扛着摄影机四处转悠。他从不征求被摄人的同意,经常是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把市场、工厂、学校、酒店和大街上的活动给偷拍下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时代,摄影师和导演无需刻意安排,就能在生活中发现无穷无尽的内容。摄影机成了时代的见证和生活的眼睛,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术语“电影眼睛”逐渐酝酿成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委员会”的规模扩充了,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这时,“电影眼睛人小组”(Kinoki team)成立了。1923年7月,维尔托夫发表了他著名的宣言《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这个宣言就像他弟弟运用摄影机的方式一样富于激情:
“我是电影眼睛,我是机械眼睛。我是一部机器,向你显示只有我才能看见的世界。
从现在起,我将把自己从人类的静止状态中解放出来,我将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我接近,然后又离开物体,我在物体下爬行,又攀登物体之上。我和奔马的马头一起疾驰,全速冲入人群,我越过奔跑的士兵,我仰面跌下,又和飞机一起上升,我随着飞翔的物体一起奔驰和飞翔。现在,我,这架摄影机,扑进了它们的合力的流向,在运动的混沌中左右逢源,记录运动,从最复杂的组合所构成的运动开始。……我的这条路,引向一种对世界的新鲜的感受,我以新方法来阐释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世界。”4
维尔托夫在这篇宣言中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摄影机比人的肉眼更完美,借助这一机械手段,人的肉眼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本雅明一定很熟悉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曾多次提及电影摄影机所具有的这一新奇功能(第11、13节)。肉眼所见的世界是混沌的,经常处于无意识状态,而摄影机却能以机械的手段对时空进行无微不至的分析。一方面,电影能帮助肉眼看到更细微的东西,如奔马的步态,手指的微微抖动,另一方面,电影还能帮助人们重新来表象这个世界,而这一表象方式既不同于日常的寻视,也不同传统的绘画。维尔托夫热衷于透过电影眼睛来揭示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发现和形成电影语言(蒙太奇)的过程:
“毕竟,看芭蕾演出的观众眼花缭乱,一会儿看彼此关联的一群演员,一会儿又漫无目的地看这人或那人的脸,看这人或那人的腿――这一连串漫散的感受,每个观众各不相同。我们不该把这呈现给观众。一个连续运动的体系要求我们拍摄舞蹈者或拳击手时,遵循他们的动作顺序,逐一摄下来,迫使观众的眼睛转移到那些不应该漏看的连续细节上来。电影摄影机以最有效的顺序,把观众的眼睛从表演者的手臂移向表演者的腿部,又从腿部移向他们的眼睛等等,并将这些细节组织成一个有序的蒙太奇研究。”5
电影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电影语言是独特的,新颖的,要注意不能让它重新落入旧事物的窠臼。维尔托夫在另一篇宣言《带摄影机的人》(1928年)中,把他的这一立场表述得十分清楚,“实际上,电影眼睛小组在抛弃了摄影棚、演员、布景和剧本之后,他们就开始坚决地清理电影语言,让它跟戏剧和文学的语言彻底分家”6。在维尔托夫看来,镜头与镜头的衔接自能说明一切,画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解说词的御用工具,“删掉一段字幕根本不会影响影片的力量”7,而即使用到字幕,它也应该与画面构成一种对位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解释说明关系。
维尔托夫对电影语言的“清理”,表面上看起来和爱森斯坦一样只是在追求一种纯净的形式,骨子里却暗含着对纪录精神的坚持和对“主题先行”的反对。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维尔托夫的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它无疑带有“反计划”的嫌疑。从1928年开始,凡是申请纪录片项目和经费,都要提前准备一份详细的“剧本”。这对于维尔托夫来说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怎么可能在进入生活以前,提前知道他要寻找的和记录下来的是什么“真理”呢?为了继续他的工作,维尔托夫不得不做出了某种妥协。但是,他到底找准了一个机会,拍摄了一部酝酿已久的电影:《带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年)。这部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直观表现,是以胶片的形式发表的一份宣言,它没有剧本,没有布景,没有字幕,也没有演员道具,它是一场寻找“真正的国际化的绝对语言”的实验,同时也是对电影眼睛人工作方式的一种示范。
《带电影摄影机的人》是一部在当时引起巨大震动,在今天看来依然富于冲击力的影片。这部纪录片体现了制作者高度复杂的剪辑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没有因此带有任何令人感到糟糕的主观性,相反,它是一部具有很强纪实性和多义性的作品。
首先,它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在影片的开头,我们看到主摄影师米哈伊扛着一架摄影机攀上一个巨大的摄影机,在他准备开始拍摄的时候,镜头闪向流动的云层下一座宏伟的电影院。电影院中是肃穆等待着的一排排座椅,随着放映员紧张的准备工作就绪,竖立的座椅自动落下,这时观众们从影院的门口鱼贯而入。在《带电影摄影机的人》的巨幅海报映衬下,一个女人从床上爬起来,晨曦中一个流浪儿在公园的长凳上睡觉,大城市的一天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看到带着摄影机的米哈伊出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有时他扛着摄影机和三角架走在拥挤的人群中,有时他站在铁架桥上,有时他在攀登一个烟囱,有时他出现黑暗的矿道里,有时站在火热的炼钢炉边,有时甚至钻到铁轨下拍摄飞驰的车轮。在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他站在一辆敞篷吉普上,从后面追击三辆马车,马车上有打扮入时的少女,英俊的军人,还有小孩和母亲,骏马在奔驰,摄影机在运动,在频繁切入的譬喻性镜头中,火车巨大的车轮隆隆起动。在另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他坐在一个滑轮装置上,俯拍汹涌而下的大江。接下来,我们还看到维尔托夫的妻子像纱厂女工那样坐在剪辑台前,随着胶片在她手上快速穿梭,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像魔术般“活”了过来。在川流不息的影像背后,我们不断看到一只眼睛,一个像眼睛一样开合的镜头,一只名副其实的“电影眼睛”,它在闪动、观察和注视着一切。我们看到电影院里的观众,看到电影海报,看到剪辑师,甚至看见一架摄影机用三角架走起路来。这的确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它教会我们如何忘我地工作,如何用电影眼睛见证生生不息的生活,如何用明白晓畅的电影语言与全世界的观众沟通。
其次,它是一部“城市交响曲”。城市交响曲是1920年代兴起的一种纪录片样式,它通常不用解说,而是运用类似于MTV的剪辑方式,把大城市纷繁复杂的生活画面快速拼切成一阕有声或无声的交响诗。瓦尔特?鲁特曼(Walther Ruttman,1887-1941)拍摄于1927年的《柏林:大都市交响曲》是城市交响曲中的典范。鲁特曼的柏林交响曲记录了柏林的生活,《带电影摄影机的人》表现的范围更大,它的镜头取自莫斯科、基辅、里加等数个城市。城市交响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试图用画面的拼贴来摹仿音乐的韵律,这使得它更注意镜头之间的横向对照,而不注意去保护事发现场的时空完整性。和默片时代的其他城市交响曲相比,《带电影摄影机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这种形式化、抽象化的倾向,但是它所指向的绝不是艺术家的个人好恶,而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和这个时代最富于特征的那些侧面。
的确,《带电影摄影机的人》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它虽然带有形式化、抽象化的倾向,但它的每一个镜头都保留了某种真实的现场感,剪辑上高度形式化的追求并没有把每个镜头的意义榨干。实际上,这是一部既注重形式结构,又注重内容的片子。它依靠镜头的排列和对比而形成的音乐性,恰好能和一个升腾着的时代对应起来。我们看到飞机和汽车从工厂大门开出来,看到火车在铁轨上奔驰,看到矿工在劳动,电影工作者在行动,纺织女工在纺纱,未来主义所赞叹的齿轮和曲轴在飞速旋转。所有这些镜头都并不是在刻意地说明什么,但我们能透过它们嗅到社会主义苏联的那股朝气,而这一点和《柏林:大都市交响曲》里的末世氛围截然不同。也许,我们可以说这部片子对生活的披露还不够深入,但它绝对不是一首粉饰太平的赞美诗,它没有回避马路上的流浪汉,没有回避像打仗一样争抢拥挤的船码头,没有回避贫富悬殊,没有回避黑市上的小贩,没有回避农妇铭刻着苦难的面庞。它既没有刻意告诉我们什么,也没有存心不告诉我们什么,它只是在记录。这双电影眼睛几乎无处不在,它在工人俱乐部,也在受到政府谴责的酒吧间,它在群众休假的海滩,也在高档的美容院,它在产妇的床前,也在办理离婚手续的柜台前,它在婚礼马车上,也在灵车驶过的人群中。它不带一丝专制和禁欲的色彩,透过这双电影眼睛,观众看到一个暴露的女郎在床前换内衣,看到一个婴儿从血淋淋的阴道里露出脑袋,看到海滩上裸露的胴体,看到美容床上的富家女,看到马车上俏丽的少女,看到一个运动员投掷铁饼时健美的身姿。
电影眼睛四处飞翔,它甚至无意间也为中国人留存了一份历史的记忆。这是一位摆地摊的中国老头,他的手轻轻一抖,就能把两个套在一起的圆环分开,他把碗一挪动,就能变出一只白鼠,在苏联儿童快乐而惊奇的面庞背后,一张饱经沧桑的中国艺人的脸就这样长久地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
1929年,维尔托夫出访巴黎,他对那里的听众说,“‘电影眼睛’的历史,是一部为了改变世界电影方向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历史,它想在电影界为非表演类的电影争得比表演类的电影更为重要的地位,想用纪实(document)来代替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想冲破剧院的舞台走向生活的广阔天地”8。维尔托夫及其电影眼睛小组,无论是对于电影,还是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有一种近乎于痴狂的激情。然而,这并不是那种令耳目昏聩的激情。电影眼睛明澈如水,它把自己放置在低于生活的位置上,如此便能真正做到俯瞰世界和在世界中飞翔。
注释:
1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第10节. 载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Schocken Books, New York,1969.
2 转引自Erik Barnouw, Documentary: A History of The Non-fiction Fil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54.
3 维尔托夫,《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1929年),皇甫一川、李恒基译,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4 维尔托夫,《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1923年),皇甫一川、李恒基译,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5 维尔托夫,《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
6 维尔托夫,《带电影摄影机的人》(1928年),皇甫一川、李恒基译,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7 维尔托夫,《带电影摄影机的人》。
8 转引自Erik Barnouw, Documentary: A History of The Non-fiction Fil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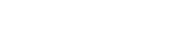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Pure cinema,一部提醒你为何热爱电影的片子。
8/10。维尔托夫以眼睛即摄影机的联想形式为基础,大力显示了剪辑和特效操控现实的威力:倾斜的画面分割两个街景再重新并置,摄影机疯狂地横移拍摄城市的不同角度,机械内部充满动感的零件运作,眨动的眼睛和数次旋转拼合下的街车、铁轨一起快速剪辑制造闪烁效果;将平凡的小细节变成魔幻秀,展现忙碌而充满生机的工业化景观,逐格拍摄的动画技巧(一碟小龙虾活过来跳动、摄像头爬上机架并说明它如何操作),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实践了赋予摄影机生命和灵魂。叙事呈嵌套结构,浅层是劳动人民从苏醒、工作到休闲的线性时间顺序,深层为观众线索,开头空旷的影院随着胶片安装上、凳子逐排放下,观众逐渐增多进入观看的状态,但时空关系被蓄意颠倒,从白天发生的事剪回黎明熟睡的妇女,还将运动员、许多勺子敲击的动作结合观众的反应,体现自我暴露的电影形式。
这片能看完我真佩服自己。主要是配乐有种把人逼疯的感觉。但构图真的太牛,对摄影大有启发,种种不对称,不中心画面几乎颠覆了我对构图的认识。
①电影眼;②纪录片与先锋片交融,酣畅流动城市交响曲;③剪辑与蒙太奇的极致,平均镜头长2.3秒;④双重复调的自我暴露,镜头中影院屏幕中观看本片关于如何拍摄本片的镜头,剪辑与摄制过程;⑤结婚,离婚,葬礼,出生,急救;⑥定格动画(自动跳舞的摄影机),快动作(流水线工人),慢镜(田径),斜切,多重曝光。(9.5/10)
Vertov美学的集中呈现,跟Epstein一样,既强烈怀疑人类视觉,又寄望于电影眼的超越性;不同的是,V的reality不是无意识而是social reality,并且有着当时苏联普遍的机械崇拜。我个人认为最有趣的地方是自反,但它却并不是布莱希特意义上的自反,相反,在V这里电影本身构成一种创造者,一种对人类感知局限的超克力量(最后的动画部分,人不见了,摄影机实现了真正的自我主体,V在《我们》中的这句话“Our path leads through the poetry of machines, from the bungling citizen to the perfect electric man”简直是一句后人类宣言),这种dehumannization恰恰与社会主义创造新人的理念形成共鸣。
虽然一直不愿意打破不给记录片打满分的惯例,但无可否认的是这部1929年的记录片以多么完美的切割镜头与双重曝光为观众留下了苏联风情画。印象最深的是女工包装烟盒,摄影机动画以及结婚与离婚的镜头,政治与政策不经意地流露在作品中,却改变了记录片的"忠实",因而呈现出与年代不相吻合的艺术。
一百年前人家就知道拍摄电影是为了记录凡常中的视觉奇迹和发现它的狂喜,一百年之后还有人在跟我说电影只是讲故事。
「破碎的三角牆,坍塌的柱子,被認為見證了這座神聖大廈承受電殛與地震之最基本自然毀滅力量之奇跡。然而,就其人造性而言,此一廢墟顯現為古代的最後遺跡,在現代世界中只能以其物質形式被視為一片古蹟如畫的觀光景點。」(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546356/)
电影唤醒现实,电影驱动现实,电影颠覆现实,电影创造现实,电影即现实。很难相信这是来自地球的作品,全程目不转睛。剪辑的终极魅力,对艺术形式及其受众的绝对信任。现场电子配乐。
确实牛逼。1,用电影来探讨电影的本质,2,摄影机比拟眼睛,多处出现。3,城市生活的交响曲。4,镜头剪辑的教科书。
记得第二章镜头突然停下来的那一刻,几幅画面后,摄影师和剪辑师对观众打起招呼,打破第四堵墙的同时再打破第四堵墙(又名打破第十六堵墙),真劲儿的配乐与鼓点,玩叠影玩蒙太奇,在城市交响曲式的叙事之上再加上爱玩的天性,实乃默片时期最酷最现代的炫技之作,纯影像的杰作。
狭隘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部完全由影像决定的电影,影像是最大的主导也是最深的基底,通过超越时代的剪辑与后期制作和更为凌厉的蒙太奇技来展现这些无序的、非线性的片段。在此,摄像机不再是死物,而是一只好奇的眼睛,摸索、推进、回想,我们透过眼睛看世界,摄像机透过镜头看着我们。
感觉电影初期的探索,除了技术方面尝试和突破外,更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和诗意。
[260]Michael Nyman配樂版本。正如“吉加·維爾托夫”這個俄文烏克蘭文混合名字的意思——“飛旋的陀螺”一樣,他的“電影眼”和城市感極強的蒙太奇確實非浪得虛名。當然,這也是一部彰顯記錄片導演精神的經典之作。假如配上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會有什麽感覺呢?
5- 百叶窗,电影眼,快门梗。第一(正片)与第三(幕后)视角混剪,从内容到技术都玩得很花:流动街拍、卧轨仰拍、快闪分娩、慢镜定格运动、分屏、眼耳蒙太奇、简易特技,甚至还有动画.... 首尾呼应的电影院设计赞。后半的剪辑和节奏大嗲,前半配乐违和。
这部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直观表现,它没有布景,没有字幕,也没有演员道具。影片呈现了一个缜密的套层结构:表层上是一部纪录苏联劳动人民平凡生活的城市交响曲,其内层则讲述了摄影机如何纪录生活、摄影师如何进行拍摄和剪辑。其实是剪辑让这部影片更有魔力。
4.5,《持摄影机的人》首先“看”到了自己与观众,在最后,我们则通过定格动画“看”到了这台自由运转的机械。它是从机械中产出的影像。机械、日常与苏联的政治宣传并置,皆为65分钟机械运动的零件。音乐的“激情”则完成了1920s的苏维埃集体统治需要:生产性与建构主义,忽略个体,高速运转,20世纪工业社会后期的未来感,如今被称之为朋克。后半段的身体—美学,似乎蕴藏着纳粹德国的里芬施塔尔和她的两卷本《奥林匹亚》
通过持摄影机的人持的摄影机,我竟然怀念起那种自己未曾置身其中的时代,但是既然未曾经历,又何来“怀念”呢?而这就是一种怀念,人是可以怀念想象的,有的时候想象比记忆还值得追寻。
酷!! 单在配乐方面 电子 后摇 军工 噪音 bigband 20时代出现这些元素实在是难以置信
同为影像本体理论家的巴赞与德勒兹对蒙太奇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巴赞认为蒙太奇很大程度上依循于主体的内在性/习惯性视点建构而出,其让观众处于被动的被引导状态,从而破坏了真实时空中的连贯性与暧昧模糊感。而德勒兹则认为蒙太奇是使得影像生成气态感知的重要途径,其指出蒙太奇所连接的影像使一种区别于日常感知的纯粹感知、一种超人类的“客观系统”(无中心、所有物质间均相互感应的潜在影像系统)被经验性地呈现出来。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提出维尔托夫在《持摄影机的人》中以一种“无界限和无距离地看”的定义使得其拥有了使用任意技巧的正当性与客观性。维尔托夫的电影眼也因此并非是爱普斯坦口中的“精神之眼”,而是德勒兹所认为的“物质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