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大概是魔鬼
水里开枪的镜头很有意思,才开始还以为是从水下往外面开枪。
2 ) 不是可能,就是魔鬼,就是布列松
这是第一部不在灾难内表现灾难(《穆谢特》) 不在结局内表现结局(《扒手》)的布列松电影,应该将本片看做一次数学书写,等号一侧是charles自杀另一侧是Charles被影像化了的命运。构成等式的法则,元素全都是不能解释又必然实在的抽象机器,谁一旦接受了这个等式也就是承认了数学不再是语言而是世界将要变成的状态。议论世界毁灭的那点陈词滥调加速也阻挡不了世界的毁灭,顶多暗示了世界过早被创造。
本片还是保留了布列松电影的基本原则:人物都是先于电影存在的,电影被创造就是为了救赎或者,更多情况下,摧毁他们。要摧毁人物显然用不到任何以因果律为基础的科学,正如愈发恶劣的污染绝对决定不了世界的毁灭,布列松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当他通过电影把毁灭事件的每块侧面都找到并且安置,那么不断被拼图的毁灭自然就会发生。举个例子:通过去教堂,布列松让Alberte&Michel, Edwige&书店里那个男人,先后出场,构成了Charles作为恋爱参与者的一个侧面。
布列松还不止一次运用了,在人物走出空间时拍摄腿和正对话的人群还没全部就位时拍摄第一个出现身体的技巧,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在叙事中给叙事找个对手这么简单。因为电影本来就具备了用叙事性替代叙事的能力:。Charles是坐Michel的雪铁龙出的门还是某个美女的敞篷车出的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会载他出门,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可以说什么,而不是我到底说了什么。然而,电影能限制人物,却限制不了自己。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是伪装成人类的超人类力量在谋划,推动一切,每个影像都是它思考的产物和暂停。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 ,人不再是面貌,而是句子,对白,他们不是在评论自己或者制造一种只有自己能欣赏的混乱, 而是在履行一种隐秘内闭的语言系统,通过与世界的同步运动,供养陈述爱情和自杀这对孪生命题需要的一切。本片的中心毫无疑问就是Charles和心理医生的谈话,这个中心再怎么突出都不为过,因为只有站上这个点,把它理解成是影片的正面,才能往前往后审视其侧面和背面。经过了审视之后,作为侧面的Michel三人就没有继续出现的必要,同样是经过了审视,之前因为在背面不能真切看到却能始终制造骚动的元素:宗教,爱欲,也被赋予了各自的结论。心理医生成为本片中第二个阻止Charles自杀尝试的人物,如果第一个流浪汉阻止Charles自杀是因为他只是个可朽的凡人,而凡人只配在现代电影当中蜷缩在侧面,那么心理医生夺下Charles手中物品的行为就暴露了他就是魔鬼本人。只有在魔鬼那里才有最彻底的,杜绝一切救赎可能的自杀魔法——让朋友(Michel)或者仆人(Valentin)杀死自己的古罗马习俗,人性+资本主义+魔鬼本人的三位一体,电影因其名义将自己献给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神话:虚无主义。
电影跟地球一样是颗球体,不可能永远只有一面接触外界,所以电影需要厚度足够的侧面来保证其前进。Michel等人确实占据了不少本来应该属于Charles的篇幅,也同样保护Charles免于因为世界的毁灭而反思乃至放弃自己的毁灭。拿那场公交车上的议论戏举例子,布列松不厌其烦地把一次短暂的急刹车分割成数个近景:司机的手,按钮,栏杆,把手,空间并没有切分(还是在公交车内),被切分的是影像而影像背后的意识依旧完好无损,并且对这种切分给出了反应:它们是同一个事件的前后。往大了看,Michel这些侧面不时在前进中恰好滚到了观众可见的位置,这就逼着观众用一种类似计数的方式来辨识哪个是Michel,哪个是Charles, 而不再仅仅只是观察和记忆面孔与名字。更高明的地方在于,这样的滚动确保了没有哪个自作聪明的观众可以预知后续,也不可以倒推先前。而布列松的模特们又是天然免去了任何个体化风险的,所以观众在观看布列松的电影过程中享受了获得了意识的终极解放:只需看到动作与动作发出者人格的相似就可以,不用纠结这个动作和人格是什么。
3 ) 08052020台词片段
“这种社会冲突是怎么引起的? 是我的正常状态,我沉默许久了。 你没从无为中得到快乐吗? 得到了,但是明显是绝望的快乐。 你内疚吗? 内疚?从没像这样内疚过,我知道我比其他人理智多了,我绝对知道我的优势,假如我做了,我在世上就是有用的,这会使我作呕,我会透露我的观点,这将会进一步围住我,我更喜欢没有出路。 街边乞讨不丢脸吗? 查理蒂使得施予者与授与者同样丢人,那不是懒惰的好借口吗? 或许吧,但为什么那样呢? 如果我的目的是有利的,人人就会尊敬我。 生存权不是活着的补偿吗? 献出生命,这也是我能失去的。家庭计划,城堡旅游,文化,体育,语言学,农牧渔夫图书馆,各种运动,怎样收养孩子,父母教室联合会,教育:0到7岁,7到14岁,14到17岁,准备结婚,服兵役,欧洲勋章(名誉职位的佩章),寡妇,疾病:付账,疾病:未付账,成功男人,老年保险金,地方发展速度,分期付款,收音机与电视租赁,信用卡,房屋修补,交联指数,增值税和消费者。 你信仰上帝吗? 我信,有可能一辈子,但是假如我自杀的话,我认为我不会被判有罪的,因为不理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 你考虑死亡有多长时间了? 我总梦见我被谋杀,我死了,但我继续被挨打,我被蹂躏着,太可怕,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虔诚的理由,时过境迁,你会认为自己是殉道者吗?仅是殉道者。当我想跳水自尽,或者扣动扳机时,我意识到真的很难。 …… 你的生命中不再有政治了吗? 拒绝一切政治。 …… 但是医生,我没病,我得的病是显而易见的。”
4 ) 布列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的电影银幕演绎
布列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翻拍,布列松貌似用着与陀迥然不同的精神内核对《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大刀阔斧地改动,在电影银幕上重新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原著中那个不谙世事、软弱天真的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阿廖沙在电影成为整个故事的中心——查理,悲剧和痛苦在他的身上聚焦,并且衍变为查理对野兽般毫无压抑的性爱和对死亡的追求。
原著《被伤害和侮辱的人们》中陀对利己主义的那种探讨和批判在影片中好似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这只是布列松的电影风格——简洁凝练的电影书写,并且排斥所有他认为是虚假和不必要的成分,大量剥除现实到仅剩下精髓的程度。而利己主义在《很可能是魔鬼》影片中随处可见,作为影片的时代的背景——能源和环境污染的遍布,查理患有毒瘾的朋友去教堂偷供奉的钱而让查理背锅,阿尔伯特离家出走后去父母家偷食物,这些利己主义被缩小到电影的各个细节上去,而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中用大量的笔墨去用对白、行为动作来凸显出某一个角色的利己主义,这可能就是巴赞所说的:“与原著相比,电影反而更加具有文学味,小说反而具有更多具体的形象。”
(回到对利己主义的讨论上来)而正是这样时代背景下的利己主义,这个软弱无能的巴黎青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对自己生活的放弃,对机械重复的现代生活的厌恶。他在这个异化的现实社会的挤压下,说出:“我梦到,我被谋杀,但是我继续被蹂躏,被挨打。”这样绝望无助的话。他对时代的反抗和抱怨是无力和软弱的,这是他悲剧和痛苦的源头,也是导致他走向死亡的原因。
查理的身上聚焦着无数的矛盾点,他崇拜米歇尔,去跟随他加入大学左翼联盟,去反对环境破坏,而他的父亲就是一位伐木工,做着破坏自然的行为;以及等等(还需要总结)而这个绝望的青年也终于说出:“我想要做回自己的权利。”但是在这个社会里,他无能为力,他也无法回到丛林中做个野人——他自己也不愿意做个野人。
于是,在这个异化的现代社会,混沌的物质生活中,面对心理医生的提问:“你没用从无为中得到快乐吗?”
查理回答道:“有,但是明显是绝望的快乐。”
在这些痛苦的矛盾和悲剧的纠结中,查理最后走向了死亡。
5 ) Serge Daney评布列松《很可能是魔鬼》
1. 电影的声音与图像从来不是一致的,图像上移动的嘴唇引导观众的眼睛去相信这种一致性。常讨论的“画内音voix in”和“画外音voix off”是技术概念、片场拍摄术语,但不适用于深入分析声音与图像的关系。
2. Le Diable probablement教堂一幕(如果布列松电影中还有某一幕这一说的话):管风琴由上方传来的声音、人讨论教义的“话语”、吸尘器由地上而来的声音。干扰、取消人言的意义,语言变为噪音。
3. 主角的失败:社会的话语/dialectiques已经不适用于年轻人的困扰,重复这种话语只是重复加重困扰。超越语言,LDP主角进入虚无、无意义、沉默 (vs. 圣女贞德超越语言听到和看到)。
4. 四种概念探讨图像和声音的关系:a.) 画外音voix off,propagande纪录片电视节目最常用的手法,评论般的声音并不影响图像,而是影响观众如何观看图像(如动物纪录片中的各种“画外音”); b.) 画内音voix in,记者摄影者从镜头外提问画内主体,信息模式变为一问一答,声音影响画内主体的一举一动和语言,不值得信赖 ; c.) 自内音 voix out,由主体吐露出的声音,由画面中器官的移动指示的声音 - 嘴唇移动,主体似是在说话,似乎画面和声音合二为一,如后期配音的电影,或任何简单的“常规的”电影,制造corps uni的假象,不可轻信;d.) “透过”音 voix through,画面主体由于构图原因被隐藏,或者人体背对观众,观众无法得到画面中嘴唇的暗示,主体不再透明、统一、易于理解,主体不透明、有厚度、一定程度上不被影像的illusion unificatrice所剥削,指向观众:看不一定是看到,听不一定是听到regarder n’est pas voir, écouter n’est pas entendre。(布列松与戈达尔和斯特劳布类似。)
5. 布列松手记:说话的器官不仅是嘴唇,还有整个身体、还有心灵。通往看不见的器官,聆听“说”这一动作不仅是观看一个指向语言/dialectique的器官。
DANEY, Serge. «Orgue et aspirateur (Bresson, la voix off et quelques autres)», La Rampe. Gallimard, 1983. pp. 138-48
6 ) 布列松的话//敌手
罗伯特•布列松:魔鬼与我 “Robert Bresson: The Devil and Me” 1977年6月13日,《快报》 L’Express
《快报》:你的影片《可能是魔鬼》没有进入戛纳电影节。评委会没有选上它,你也拒绝参加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你的决定是对他们的决定的一个回应吗?
罗伯特•布列松:我本不想让本片参加竞赛的。出于对我的制片人斯特凡•肖嘎杰夫(Stéphane Tchalgadjieff)的尊重,我同意提交。它落空了,我是很激动的。我曾经爱五月的戛纳,到海里游泳……如今水已经被污染了。
《快报》:而污染是你的影片的主题之一,导致人性的堕落的灾难之一,你从中认出了魔鬼的手。你与魔鬼的关系如何?
布列松:我的生命中有两次感到他的存在。在我们制造的这混乱背后,我只是自然而然地感觉到魔鬼在起作用,而我的影片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快报》:你说的混乱是什么意思?
布列松:你记得迈克尔•科林斯(Michael Collins)从月球回来之后所说的吗?“不要破坏我们的星球,不要弄脏它。它是个奇迹。”更不消说生命的机械化了,这是真正的邪恶。不过这话题太大了……
《快报》:那么你的影片是意为一个警钟吗?
布列松:我衷心希望年轻人能调动他们的青春的所有力量对抗那正在毁坏世界的破坏性力量(他们是要为其付出代价的)。但这也许太晚了。
《快报》:而你相信一部影片也许会导致一场良知的危机,甚至是一场运动?
布列松:人们毫无困难地接受着电影中的流血与折磨(甚至还有其他地方的)。但这是关乎一种原始的、将我们带回最基本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的东西的。
《快报》:你是否在试图动员这些人?
布列松:时不时地,就有一位年轻人将自己浸满汽油,然后在高中的院子里将自己点着——正如几年前在图尔宽(Tourcoing)发生的那样——而没有一个人能阻止他,或预计到他将要做什么。全为了引起人们对正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中的恶心的事情的注意。
《快报》:而那些东西是赤潮,死亡的小海豹,被屠杀的雨林,激增的人口,核战的威胁,教会与国家的失败,毒品,精神分析:你的影片中展示的这一切弊端是为了阐明你的主角的智识道路、最后的举动?
布列松:年轻人必须拒绝服从一种会毁灭一切有产生喜悦的潜力的东西的生活观念。但我们能让时光倒流吗?
《快报》:通过使用非专业演员,通过将非常年轻的少年们放置在这种启示录式的语境中,难道你没有冒上使他们受到精神创伤的风险吗?
布列松:这个想法折磨过我几天几夜,然后我意识到他们的年轻心志能获得胜利。
《快报》:然而你有着用强硬手段指导你的表演者的名声?
布列松:也许在我的早期影片中是这样。如今我几乎完全不指导他们——越来越少。我给予他们许多自由。
《快报》:你信任你所选的人,但你选得很谨慎。
布列松:有时候我会犯错误。为了本片,我面试了大约六十位年轻人,还有十多位没那么年轻的。声线是最重要的,我反复说过这一点。
《快报》:你的主角有轻微的发言障碍。你也是。
布列松:我觉得这很可爱……但并非因为这像我!
《快报》:而且他还看起来像你。而且他有你走路的样子。在影片中看到他,很容易会想:“这想必是布列松以前的样子。”
布列松:真的吗?有意思……
《快报》:年轻的布列松是什么样的?
布列松:说得好像我能够告诉你似的!暴力的?绝对主义者(absolutist)?过度的?许多烟酒。如今我不碰酒也不碰烟了。
《快报》:你向年轻人宣扬革命?
布列松:在街上游行是没有意义的。警察仅是比一百年前就有力与众多一千倍。在我看来,貌似年轻一代彻底改造世界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一种凶猛的,但又是消极的,对抗。
《快报》:谈起一场战斗就是谈起一种敌人。
布列松:敌手是轻佻的乐观主义;是理应使一切安好的金钱;是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喧嚷的群众;是权力的至高无上。
《快报》:你是否会制造你自己的敌人?
布列松:如果是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走在正道上。
《快报》:你是否认为本片是它之前的那些的符合逻辑的延续?
布列松:我不认为我所做的事之中有太多逻辑。而且我所制作的影片在我看来貌似并不能合在一起形成人们称之为作品集的东西。我进行尝试。我将目光专注于我所相信会成为一种了不起的电影书写的东西,一种为了明日的书写,通过图像、运动与声音。不过我在其中越久,那片视野就越是隐退。我对我的影片的重要性产生怀疑。因此我常常感到需要得到他人的支持。我希望拥有画家与雕塑家曾经所有的:一间工作室。我会不去提供任何指引。我会跟任何上门见我的人交谈。我会告诉他们在三部影片中当过导演助理是不会被带入电影书写的门的。我会使他们想去看,去听。去集中注意。技巧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有话想说,就算你说得很糟糕,那也是好事。如果你没有话想说,那就是个坏兆头。我会在我自己的影片中给他们事情做,依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不过我也怀疑我能否建立起那样一种情况。我不知道。
注释:
快报(L’Express)1953年发刊的法国新闻类杂志,政治倾向原来是中间偏左,后来比较居中。
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 法语为Quinzaine des Réalisateurs)成立于1969年的与戛纳电影节相平行的独立的影展,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由法国导演公会(Société des réalisateurs de films)举办的,起因是回应当时戛纳电影节的取消,作为一次与罢工工人团结起来的举动。
斯特凡•肖嘎杰夫(Stéphane Tchalgadjieff, 1942-)美国制片人,生于保加利亚,主要制片工作在法国。
迈克尔•科林斯(Michael Collins, 1930-)美国空军军官、试飞员、航天员,生于意大利。是阿波罗十一号(Apollo 11)的指挥舱驾驶员,在其1969年的登月任务中,他待在绕月轨道上。
图尔宽(Tourcoing)法国北部市镇,邻近比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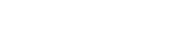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很可能是魔鬼,将不属于我生活的影像和事实使我知晓而又无能为力,很可能是魔鬼,把精神的和现实的救赎都弄得不再可以承载希望,很可能是魔鬼,它让我连自我都难以了解,我的过往、记忆和希冀混乱不堪得理不出存在的依据。我很可能是魔鬼。局部的特写彻底解放了疏离的魅力,我们不再幻想这个动作是由我观照的客体发出而服务一段故事,它片段地打开一个纯粹客体的窗任由我们进入,听取秩序者的鸣笛和叫骂,伴随着圣乐砸开教堂的钱箱。它令我动弹不得。<4.5>
正如影片本身所表现出的失措、虚无、漫无目的,忧郁的年轻男子在经历了社会与自我的多重崩溃之后陷入了一种绝望的混乱和无序,于是把人生无意义归咎于神秘主义的魔鬼作祟,一遍一遍毫无表情地向这个世界表达温吞犹疑的反抗,就连死之前都还在试图谈论自己无用的怀疑,布列松却不留情面地让他一枪毙命。
布列松用令人窒息的影像近乎绝望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青年存在主义的命题和虚无主义的泛滥。演员木偶论完美地契合了电影的深层所指,向我们呈现了现代青年被社会异化到身体和灵魂都备受折磨的虚无状态。在布列松标志性的局部特写中,这些青年成为绝对的主角,其他所有人物只是服务于剧情的工具,所以一个部位的特写即可代替。极简主义造成的画面内容缺失由声音进行弥补,影像上的空缺代表人物内心的空虚,而先于影像的画外音则进一步渲染了这种空虚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物质的过剩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布列松巧妙地将电影置于这个时代背景,提出对环境破坏,核武器威胁,宗教信仰缺失,爱情观畸形等社会问题的思考,最终引申出当代青年急于找寻自身存在价值与人生意义而又无法找到出路的焦虑与迷茫这些问题很可能归结于魔鬼,毁灭可能是唯一出路
布列松创作的后期,显然已摆脱了形式的束缚,虚无主义的特质涌现在电影的各个方面。比起早起对人性的关注,这部电影的格局更为宏大。气质同样更加飘忽。对人类未来表面的忧虑下,更真切地涉及到存在和虚无的终极问题,主角最终以死亡对抗虚无。毕竟世界皆有主观念头创造,生死又有何妨?
3.5布列松的演员永远和橱窗模特一般 政治在他手里一点激进意味也无 留下只是世代的记录而已 就算自杀这样煽动的结尾也可以拍的如此克制而干净 女生都很美好 一片 pale and frail
作者纬度里为数不多的有鲜艳时代背景的作品。冷战后期的核恐怖、后工业化环境污染、宗教规劝的无效,布列松仍然机械地将时代热点“冷”处理了。只是这一次电影中的主角呈现出了某种异质性:巴黎青年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知识分子式的高度自觉,心怀人类的悲悯不如《乡村牧师日记》般具有普世性。这可能也是李沧东的某些作品的问题所在:批判时代症结的锋利或许会在病理性上停留过久,从而使得具体情节桥段功能性过强。
纪实主义与强烈现实感的粗暴介入,让冷静的布列松也不可避免得卷入滚滚的左派浪潮中,当然导演本人的态度与观众们接受感不可同日而语,「很可能是魔鬼」的确是当时人类对于世界乱相的直观心声,叛逆的青年人与革命则是另一种毁灭世界的魔鬼,只是如今看来连叹息都泯灭了。
主人公在不停的寻找生命的意义,从宗教,从政治,从爱情,其间又涉及了很多人类破坏,污染毁灭环境的东西。在寻找的过程里,那个男生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想的越多,越没意义,最后只有去死。
许是布列松真不是我的菜, 许是我对剧情真的不感冒, 许是中文字幕实在太差, 反正我是不知所云, 我....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对我来说, 此片绝对是魔鬼。
以前会觉得布列松过于冷漠 现在觉得他是超脱人类集群的理性和客观 虚无一切都是虚无 爱情政治宗教都是可有可无 当我真正完全的厌恶这个世界 才发现他的描绘是如此恰如其分 失望的尽头是否是虚无抑或反之整部色调都青青暗暗 素寡疏离沉闷无望戛然而止的死亡是必然 讲不完那句话 甚至会在他转头后毫无征兆的开枪结局 便也只能以死亡作为结局和出路 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方向
某种对于"现代性",甚至"后冷战"、"后现代"回应、萨特存在主义或唐璜"行为"只代表其自身的机械仪式,但个体叙事及其倒叙结构在被布列松泛化为人类、自然的向死而生,关于灾难与环境问题纪录影像超验地并置,自然冲动之于人类社会之喻退隐,取而代之增加由存在主义通向(或"回归")自然
从来没有觉得布列松如此虚无主义过。难得地对于电影内大段深而远的对话有了初始的理解(至少说共鸣)。感觉是某种观影上的转折点(又或许不是)。决定在看伯格曼之前(或同时)要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黑塞了。
小莫23号钢协第二乐章主题响起在恰到好处
感觉上和 温柔女子 接近,只不过讲的是关乎政治和宗教的另外一个故事。很意外的倒是最后响起了音乐,迷茫的青年用布列松的无表情的模特来表现刚刚好。
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权利?金钱?享受?堕落?...不,不会是这些。梦想?梦想一旦实现就没有意义。爱情?爱情一旦获得就会失去。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厌恶生,却也不渴望死。意义,生的意义,死的意义,那意义不在生也不在死,而是超脱于此之外。
长发少年很美,背着蓝色布包。画面简洁,色调舒服,基本都是中景,只能看到下半张脸,让人感觉压抑局促,却和整体孤独忧郁感很吻合,这种表达方式很独特,波兰海报多贴切
主题对象延续自新时代美国弥散而来的“垮掉的一代”,布列松以惯常的行动聚焦封闭住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意志,无限重复“移动步伐-游荡街头-回到房间”的步骤,其中的每一步都透露着无所指的焦虑和空洞,偶有情爱、辩论、表达,也如无形青烟一般不具有推动力量,无法让镜头跳出封闭来,也就止不住三重空间的循环,直到最后借助毁灭的科技(手枪)结束于三重时空外的黑夜墓地。“要和平做爱而不要战争”的嬉皮士精神并未带来如数学般精确的答案(片中以数学指代科学),战争永远在发生,危险永远存在,政治抑郁和个人存在危机相互绑定,无法根治,数学和精神分析都是短暂的自期,自我到底如何存在于个体和政治的两者间,才决定了和平的正当性和做爱的有效性。(布列松极简主义的意义指向反而是最丰富的,不进行心理归因的行为主义可拥有无穷释义。
布列松倒数第二作,获柏林评审团大奖。1.布列松最有时政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在刻画一个遍寻生活意义无果的青年大学生的最后岁月的同时,插入了多段纪录片影像,如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统计报道(棍击小海豹残忍),以及课堂上对核电站风险的讨论和教堂内对天主教难以适应现代生活的质询。2.尽管是彩色片,但无论是服装还是环境空间均为冰冷肃杀的色调(棕、灰、黑)。3.对肢体动作的大特写,人物冷漠空洞的神情,以及爱情、政治、宗教、心理治疗等多方面均无出路的体验,浓浓的虚无感至终渗入了观影者心中,结尾话未说完的猝然死亡则更彰显出无情的世事冰冷。4.对伐木树倒的镜头的无尽叠加,噪音,间或插入主人公紧捂耳朵的近景,令人窒息。5.在教堂里播放着赞美诗乐,瘾君子却在狂盗捐赠箱的硬币,如此绝望地呈现出赎救的不可能。(9.0/10)
@arsenal berlin 布列松对于人类社会的冷眼到这个阶段已经趋于全面绝望甚至残酷,在他看来什么都无法带来拯救:政治不能,科学不能,宗教不能,爱情也不能。资本利益驱动下人性如薄冰,一碰即碎。大量机械运动的特写(电梯、公交车门、开锁等等)与人的行为并列出现,使得人物的僵硬与漠然更为突出。
4.0。1.一个忧郁的巴黎青年注定要死,宗教无意义、环境无意义、爱情无意义,甚至连存在都无意义。2.68年5月风暴之后,布列松的思考也接近于戈达尔,甚至于主人公的行事动机。3.极简风格省略太多,不少情节需要脑补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