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越战后期,美军上尉威拉德(马丁•辛 Martin Sheen 饰)奉命沿湄公河而上,搜寻脱离美军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的科茨(马龙•白兰度 Marlon Brando 饰)上校,将他带回或杀死。科茨上尉曾经是美军在越战中的英雄,战功赫赫。然而,忽然有一天,他失踪了。随 后,情报指出他在柬埔扎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军队,专门反对美军。 威拉德与几名士兵一路沿河而上,途中他们目睹了种种暴行、杀戮,目睹了无论美军士兵还是当地人在长期的战争中精神扭曲,做出的种种非正常的行为,威拉德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威拉德最后在柬埔寨科茨的王国中被当地人捉住,见到了科茨。然而,科茨竟欲求一死,叫威拉德将这里炸为平地……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天亮·分手极限职业美国众神 第二季呼叫助产士 2024圣诞特别篇快乐星球 第三部西游奇遇外传跟我走吧真爱之吻可爱的小农场第一季新的一课风中的低语我们第一季致命佈局芝加哥急救 第八季死神假期1934圣诞奇妙公司英语邻家性士第一季孟婆传说传真人谜探休格人生路不熟袭击黄金七令之罗刹风云破胆三次5:血光再起世界上最强的男人嫌疑人X的献身2017京都人秘密的欢愉双重
长篇影评
1 ) 战争让人疯狂
在这部影片里,科波拉以其雄浑稳重的拍摄风格将炮火连天的越南战场,巍然塑造成一座充满暴行和杀戮的人间地狱,他探讨的是这场残酷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影响,透过了疯狂的柯兹上校的残虐来表现出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心智是如何逐渐丧失的。马龙白兰度所扮演的那位滥杀无辜的柯兹上校,被科波拉塑造成为一个在越战中渐渐对血腥麻木了的人,他沉浸在腥风血雨中,无法改变只能屈从,但当前来暗杀他的维勒上尉出现在他眼前时,轲兹上校却没有杀他,反而借助维勒上尉的手完成了他渴望已久的死亡,对于他来说,也许这才是最好的解脱方式。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秉承了原著《黑暗之心》的,他是十恶不赦的“统治者”,推行野蛮、血腥、非人的残暴统治,但又那样的渴望解脱,影帝马龙白兰度完整地缔造了这个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的人,他演绎的柯兹上校和那句“你有权杀我,但是没有权力审判我”的台词已经深深地刻在众多影迷心中,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影像。原文出处:http://t.cn/R0QsTmh
2 ) 自由的尽头
威利上尉是优秀的军人,但是战争在锻造他的同时也给了他无法磨灭的烙印。他已经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他只有渴望回到战争中去,终于下一个任务来临了。他奉命回到越南战区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找到意外叛变的古华特上校,说服他或者杀死他。一路惊险离奇的旅程,威利越是接近古上校就越是理解、敬佩他。当他真的见到已成为一个光怪陆离王国首领的古华特,古华特却希望威利上尉杀死他。最终威利成全了古华特。影片在“恐惧”“恐惧”的歌声中结束。和我一起坚持看完这三个多小时《现代启示录》的朋友说,片中除了威利,所有人都疯了。为了找一片冲浪的海滩,率领直升机群瞬间屠杀一个村庄的高比上校;恪尽职守导致误杀一船人却还企图施救的伪善的队长;拿着M16却整天想着怎样调配美味酱汁的胆小厨师;完全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乳臭未干的孩子;同样迷惘的青年冲浪手兰斯;甚至花花公子的妓女们;更不用说生灵涂炭的古华特上校,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疯狂。仔细想想,威利的正常和冷静何尝不是疯狂呢?在如此混乱的世界里保持理性,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一项军事任务,甚至最后有成为神的机会,却理智的离开,这难道不是另一种疯狂吗?
骑兵团上校高比让我想起《拯救大兵瑞恩》里在炮火中寻找自己胳膊的士兵,他逃避现实,在他眼里早就没有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争了,这一切只是一次海滨度假。古华特的精神和意志高于高比,但越是冷静的人疯了,越是可怖。古华特是绝望的。一开始他坚信自己的正义与理想,相信战争的正义性,但是当他真正经历过战争,直面人性的恶,黑暗的心,他才疯狂了,这是理智导致的疯狂,前面说到威利疯了,他在应该疯的时候理智,所以我说他疯了。古华特才是正常的人应该有的状态,战争的双方都让古华特感到绝望,古华特先是对美国失望,不想再做美国军人,然后是对越南失望,不想做越南杂牌军领袖,最后他对自己也失望了,他决定不再做自己。
前阵子姜文在崔永元的节目做客,姜文说,“之所以要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因为人们有很多角色,你其实不知不觉的一直在扮演着,他们现在扮演观众(指观众席),其实他们本质上不是观众。你给人搁那儿了他只能演观众。还有扮演儿子,扮演女儿,扮演父亲,扮演恋人,其实这都是角色。最好(的状态)就是把这些角色都拿掉,但是到四十来岁你想拿掉的时候,你不知道拿到哪儿算完。拿一个还一个,拿一个还一个,不知道哪儿算摘干净的时候,你开始恐惧了……我们就是从这儿开始,来拍《太阳照常升起》。”
古华特做到了,他把一切都放下,把人之所以是人的一切都放下,他获得了姜文说的那种“最好的”,彻底的自由。他成了神,但是在成为神之后,他发现他堕入了更绝望的境地,绝对的空虚,神的空虚。看着那些膜拜者,他甚至在本子上狠狠地写“把他们都炸死吧”。当成为神,彻底自由的时候,只有无聊。“限制产生力量,自由导致死亡。”(达芬奇语)古华特只剩一件事情可做了,那就是死。但神是不能自杀的,因为神的精神和意志他不能自杀。他只有渴求死亡,渴求被谋杀。直到威利到来。
反战题材千千万万,科波拉之所以是科波拉,还因为他将惯常题材表现的丰富多彩充满层次。我不认为这三个小时里有什么部分是多余的,包括威利和法国女人的床戏。科波拉把这个肮脏而龌龊的故事打扮的花枝招展。从美国本土一间中产阶级的房间开始,燥热的越南前线指挥办公室,直升机轰炸雨林瓦格纳冲浪板,丛林中探出头来的一只老虎,劳军花花公子妓女,烟花一样的炮火,最后直通向神秘诡谲却充满异族邪教美感的王国。这故事是启示录,也是寓言,我们的现代社会虽然被科学打扮的五彩缤纷,但是在绚丽背后,一样隐藏着无数绝望的眼睛、黑暗的心、迷惘而混乱的宗教。现代国家,你们也许战胜了古特华上校,那么你们就抱着科学的金枝,准备过胆战心惊的守卫圣树的生活吧。
已刊载《看电影·午夜场》2012年第1期
3 ) 《现代启示录》剪辑师 | 剪辑就是漫长的亲密行为
本周五(12.27)19:30 改编自康拉德的《现代启示录》在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报名详见文末。参与本周活动的会员有机会获得赠书《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康拉德》。
编者按:2019年是《现代启示录》的四十周年,这部伟大的作品如今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作为剪辑师的沃尔特·默奇,与《现代启示录》之间这场长达数十余载的羁绊就好像是“漫长的亲密行为”。从1979年版的《现代启示录》,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导演剪辑版,他将被删除的片段更加有机的融入电影之中。他将剪辑当成一种全身的舞蹈。本文内容节选自《剪辑之道》以及《眨眼之间》,概括性地阐述了沃尔特与《现代启示录》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于剪辑的深刻领悟。

沃尔特·默奇,新好莱坞运动中最为知名的音响设计师和剪辑师之一,也是美国70年代崛起的“学院一代”电影人,被誉为好莱坞名导背后“看不见的大手”。在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技术期间,他与弗朗西斯·科波拉和乔治·卢卡斯相识,成为了科波拉在旧金山成立的西洋镜电影公司的早期骨干。沃尔特因在《现代启示录》以及《英国病人》里的创造性贡献而在奥斯卡梅开二度。
沃尔特·默奇在《现代启示录》中创造了音效设计的概念,并将电影音响从辅助性角色提升至了独具艺术力量的高度。同时,沃尔特在《冷山》中开始使用苹果公司的低成本剪辑软件Final Cut Pro,直接推动了世界独立低成本影片的制作。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却唯独对电影史知之甚少。科波拉评价他有着堂吉诃德式的顽皮风格。

以下文段节选自后浪出版公司于2012年8月出版的《眨眼之间——电影剪辑的奥秘》中的《01 剪切——可见与不可见切口》,作者为沃尔特·默奇,译者夏彤。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剪辑是浩大而缓慢的工程
总是在事物的极端情况下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事物的中间状态,比如冰和水蒸汽可以比液态的水能展示更多水的本质。虽说任何值得拍摄的电影都必将是独一无二的,但毕竟每一部电影的摄制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谈论什么是电影拍摄的“正常情况”几乎就是误导。《现代启示录》按任何标准来说,不论制作期限、投资还是艺术野心、技术创新,都可称得上电影制作的冰和蒸汽一一整个影片耗时如此之久,我花了整整一年来剪辑,又用了另外一年来准备音效和混音,后期制作所耗费的时间是我参与过的电影中最长的。
这或许可以稍微提示一下,电影制作中什么是“正常”或什么可能是“正常”的。之所以会有那么长的制作周期,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素材量巨大。125万英尺(38.1万米),相当于230小时的素材胶片,想想最后完成的影片长度约2小时25分钟,片比差不多是95:1也就是说,每95分钟的素材有1分钟最后会呈现在屏幕上。作为参照,剧情长片的平均片比大约是20:1。
在那95:1的风景中跋涉,无异于穿过一片密不透风的森林,偶尔能见到开阔的草地,然后又迷失在厚密的树丛中。比如直升机轰炸那一段,素材保障度实在太高,而其他场景的保障度相对低多了。我相信光是基尔戈上校的场景就拍摄了22万英尺(约6.7万米),在最终完成的影片中占了25分钟,所以这段的片比高达100:1。但是很多过渡段落就只有一个主镜头——弗朗西斯用了太多的时间和胶片在主要事件上,只好用最少量的镜头处理那些过场戏段落。
举个大场面作例子。直升机高声播放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进攻越共那一段,是按照一场实战事件设计的,所以完全是按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而不是按照一系列仔细构图的单个镜头来拍摄。其编排需要大规模地调动人员、军械、摄影机以及景物本身,这就像是把一个恶魔似的玩具上好发条然后放手。

当弗朗西斯大喊一声“开始",电影拍摄就变成了真正的战斗:八架摄影机同时运转,有的在地上,有的在直升机上,每一架都装着1000英尺(304.8米,11分钟)的胶片。拍摄结東后,除非有什么明显的大问题,否则摄影机的位置就换一下,然后全部过程再来一遍,然后再来一遍,然后再来一遍,一直拍到他们觉得有了足够的素材为止。每一次都会拍出8000英尺(2438.4米),相当于一个半小时时长的胶片,没有任何两个镜头是相同的,简直就是纪录片的覆盖式拍摄。
无论如何,在最后,当电影稳稳当当进了影院,我坐下来琢磨,我们(好几个剪辑师)总的工作天数除以电影成片中总共的剪切数量,得到我们每人每天平均做出的剪接动作是......1.47个!
这就是说,如果事先基本知道我们的剪辑方向,那么耗费同样多的天数,而每天只做出一个半剪接动作这样的事情,就相当于我每天早上到那里,坐在発子上,做一个剪切,想一想下一个剪切点,然后回家,第二天再回来实施昨天想过的那一个剪切,然后再剪一下,然后回家,一直到花了同样多的时日,完成剪辑全片的我的那一部分。
由于这一个半动作本身仅仅需要不到10秒钟就可以完成,所以《现代启示录》众所周知的特殊性作为参考可以让人夸张地大松一口气,但电影剪辑,就算是“正常”电影的剪辑,也不是仅仅把素材“连接起来”那么简单。

它是发现一条道路的过程。电影剪辑师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花在实际地“剪”或者“接”的动作上。
但对《现代启示录》而言,由于题材的敏感、非同寻常的大胆结构处理、技术层面上的种种创新,以及每一个参与者都觉得有义务做到自己的最好水平,所以事情最后的复杂程度被加倍放大了。而最重要的是,尽管本片有着巨额的预算,题材的涵盖面也相当广阔,对于弗朗西斯而言这却是一部个人化的电影。很少有电影将如此多的特质跟个人的野心交织在一起。对应于成片中的每一个剪切口,可能都存在着十五个隐形的剪切口一就是那些曾经剪开,后来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又逐渐重新接了回去的剪切口。
就算除掉这些,每个工作日里剩下的11小时58分钟都花在各种各样扫清障碍、照亮前方道路的活动上:试映,讨论,倒片,再回放,会议,修改日程,被修剪下来的碎胶片的存档,记笔记,记日志,以及无数心无旁的审慎思索。光准备工作就有这么巨大的工作量,只为了顺利到达那短暫瞬间的决定性行动:找到一个剪切点,那是从一个镜头转向另一个镜头的时刻,它应该看起来完全自然、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如果它真的还能被注意到的话,就应该是如此的。

以下文段节选自后浪出版公司于2015年2月出版的《剪辑之道——对话沃尔特·默奇》中的《引言》以及《对话|壹 旧金山》,作者为迈克尔·翁达杰,译者夏彤。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时隔 22 年的重剪
2000年春,沃尔特·默奇应科波拉的请求开始重剪《现代启示录》。1977年至1979年间默奇一直在做这部片子,当时他既是该片的声音设计师,又是负责画面剪辑的四个剪辑师之一。二十二年之后,所有素材,都得以从深藏的地窖中找出来,重新受到检视(包括被抛弃和“遗失”的场景,以及所有音效资料,它们被小心保存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几个石灰岩山洞中,洞内温度和湿度都有严格的控制)。此时此刻,《现代启示录》已经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生根,所以某种程度上说,这对于重剪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在美国西洋镜公司跟沃尔特相处了一天,次日我在旧金山跟小说家阿尔弗雷多·维亚(AlfredoVéa)共进晚餐时,向他提起重剪《现代启示录》的事,维亚马上就背诵起马龙·白兰度那段“刀片上的蜗牛”的独白。晚餐过程中,维亚又惟妙惟肖地模仿丹尼斯·霍珀的唠叨:“他们会怎么说这个人?会怎么说?说他是个好人?是个有智慧的人?……”维亚曾参加越战,对他而言,《现代启示录》是代表了那场战争的唯一电影,是艺术的结晶,影片为他捕捉到了这场战争的精髓,并为他提供了一种可资参照的神话结构,告诉他自己曾如何历经沧桑,并让他在后来的岁月中能把自己写进诸如《诸神的乞讨》那样的书中。所以那些为新版《现代启示录》工作的人们,很明白把这样一部“经典”之作拆散了重新建构将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已经是美国人的公共财产了。
“它确实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默奇说,“那不是一条单行道。你们写作的人也了解这个。作品对文化产生影响,文化对作品也同样产生神秘的作用力。即使是同样那几卷胶片,《现代启示录》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跟在1979年它发行前的那一秒钟相比,已经迥然不同了。”

发行新版本的想法最初源自科波拉想出版一张DVD影碟,以便把好几场重要的场景添加回去。在1979年的版本中,由于影片时长的限制,这些戏份都删除了。同时,2000年又是西贡陷落的二十五周年,所以重新评估最初的剪辑决定似乎也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当年做出剪辑方案的时候,战争的创痛尚在灼烧着美利坚的灵魂。既然是出DVD,与其把恢复的场景单独一段段罗列出来、放在各自的章节后面,为什么不把它们按最初的设想有机地融进电影整体中呢?问题是那些删除段落的画面剪辑和音效工作本来就没有完成,特别是有一场戏,当年决定要删除它时,它根本还没有拍摄完成。所幸的是,底片和原始的声音素材都完善地保存着,它们还保持着当年从洗印厂送回来时的一卷卷胶片的状态,二十年后它们还可以被取出来使用,仿佛是几个星期前才刚刚拍摄的一样。
于是沃尔特·默奇在旧金山开始工作,就在西洋镜公司的老楼上。基本上他的工作内容是收集和重新思考在1978年剪辑时放弃掉的三个大段落的材料:一段是空运《花花公子》的兔女郎们,一段是白兰度在库尔兹营地更深入的几个场景的素材,还有一段发生在一块法国殖民者的橡胶种植园里,那是一段诡异的丧葬晚餐和床戏。
“影片在缺少那些肢体的情况下,却获得了一副躯干,”默奇在谈到那些遗失的戏份时说,“而现在,我们要把它们缝回去,谁知道会怎样?躯干会接受它们吗?拒绝它们吗?还是会觉得它们很麻烦?这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我感觉应该还行,事实上进展得也还不错。但还是得等到最后,当我们能退后两步,看到作品的整体面貌时,才能说这样做在艺术上究竟是成功,还是仅仅满足了一下人们的好奇心而已,因为他们对这部电影本来就很感兴趣。”

那三场戏是新版本中增加进来的主要内容,但默奇和他的同事们还进行了很多其他的细微调整,加入的东西为影片的大部分内容带来一种不同的调子。多了些幽默,而且很多段落之间的过渡场景在之前的版本里都因为时间的因素被剪掉了,现在把它们加了回去,使影片整体不再显得那么碎片化。默奇说,那些被拿掉的材料“是一场场惨烈激战的典型牺牲品,这些激战在每个剪辑室里都在发生着:影片可以短到多短还能成立?虽然弗朗西斯握有定剪大权,但他跟所有人都同样清楚面临的限制,必须让影片尽量瘦身才能挤进电影院去。而对新版本而言,那种压力、那种压缩高于一切的原则,现在变得没那么紧迫了。”
旧金山的对话
翁达杰:你是一位在声音和画面剪辑两个领域都卓有建树的剪辑师。你为《现代启示录》这样的电影创作了“声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声音的景观产生兴趣的呢?
默奇: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一直如此。我对声音的感觉与人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我的耳朵张得很开吧。每当语言让我挫折的时候,我就会转向音效。如果我不知道某种东西该叫什么,我就会模仿它的声音。
大约就在那时,磁带录音机的商业化已经普及。我有个朋友的父亲买了一台,所以我就没完没了地往他家跑,去玩那台录音机。那种狂热简直是对录音机潜力的彻底痴迷和无比沉醉,我深陷其中。有一天,我终于说服父母买了一台这样的录音机放在家里,因为可以用它从电台节目录制音乐,再也不用去买唱片了。结果呢,我几乎没有拿它去录什么电台音乐,而是把麦克风伸出窗外,录起了纽约城的声音。我还曾把一堆金属摆出个什么阵势,用胶带把麦克风粘在上面,然后在金属的不同部位又敲又擦,简直好玩极了!接下来我发现了在录音磁带的胶带实体上进行剪辑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把磁带的不同部分分别剪断下来,重新排个顺序再粘回去。

翁达杰:你真的想过去搞什么自然科学吗?
默奇:倒没有。不过我对科学很感兴趣——我对数学很感兴趣,它是对隐秘形态的揭示。而作为一个剪辑师,你要做的就是同时在肤浅和深刻的各个层次上发现各种有规律的形态,至于能深刻到哪一步,就得看你自己了。
事实上,拍摄出来的电影素材永远都比最终影片能用到的要多得多,平均而言是后者的25倍,也就是说一部两小时的电影会有50小时的素材。有时候这个比例是100∶1,《现代启示录》就是如此。而电影几乎都是打乱了顺序拍摄出来的,这是为了使摄制的效率更高,但它却意味着必须有什么人——剪辑师——来肩负起一份责任,在那多出来的海量素材中找出最佳材料,并将它们以最正确的顺序排列出来。而“最佳”和“正确”这两个小词含义的复杂程度,堪比整个气象万千的宇宙。
要想让电影剪辑——也可以简单地称作“电影建构”——真正发挥功效,就必须找到声音和画面素材中那些隐秘的图案,并好好利用它们。(本节选完)
感谢 后浪出版公司对本文的授权

扫码报名参加活动

国际影像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VCD 影促会)于 2017 年夏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它致力于搭建一个观影、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向公众普及和推广艺术影像。一方面,VCD 影促会以举办影像资料展、文献展、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方式为更多人提供影像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它也通过自身平台挖掘更多优秀的影像艺术作品,在为其提供放映机会的同时助力青年影像艺术家持续创作。四季影展Lumen Quarterly四季影展是VCD影促会的主要落地项目之一,它立足于长期稳定地为观众展映高质量的艺术影像作品,并通过主题论坛,讲座,文献梳理等方式优化观众的观影体验。此影展更加看重个人经验在文化有机体中的作用,并试图由此出发,以最开放的态度,将艺术电影、实验影片、短片、动画、影像艺术等多种类的影像作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此,影展以我们所熟悉的春、夏、秋、冬为时间轴展开,每三个月邀请一位艺术家或文化人担任策展,按主题挑选影片,长期不间断地进行展映。通过这种穿插,比照式的放映方式,VCD影促会希望能够开放性地引起话题,使观众从更丰富的层面和更平易近人的角度对影片以及动态影像本身产生更多的认识。
4 ) 伪经与残篇
不过因此科波拉也付出了代价,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影片的上映,直到科波拉同意删减掉相当一部分的素材。尽管如此,1979年公映的153分钟的版本也已经算是鸿篇巨作了。即使这样,在许多痴迷与本片的“信徒”中,这本启示录是不完整的,他们一直呼吁科波拉赐予他们完整的启迪。于是在2001年,这个美国历史上敏感的节点,科波拉重新剪辑制作了196分钟的2001重映版,比原版足足多出了43分钟的补充镜头,而窥过这些镜头,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社会政治在这21年来发生的变化。
一.湄公河之歌
玛格丽特▪杜拉斯经常在她的小说与电影常常中强调一种乡愁:这些高卢人的后裔喝着湄公河的乳汁长大,却被亚细亚与欧罗巴双重抛弃,成为将记忆作为自己唯一的故乡。而《现代启示录》在2001版本增补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这些坚守着自己“土地”的法国殖民者后裔的描写。
本片原著,即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没有强调这个问题的,因为《黑暗的心》的故事背景是雨林丛生的热带非洲腹地,白人们并没有试图政府驯化这片土地,而是仅仅掠夺象牙资源而已。但是《现代启示录》中,并没有简单的将白人殖民者脸谱化,在揭露美国侵略实质的同时,也提到了这个尴尬的问题:我们如何那些的确以西方先进方式开发了土地的殖民者?
在增补的片段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这些法国殖民者的,这些殖民者和神出鬼没的越共成员一样,都是在雾气中出场的。而接下来出现的一场对话戏,其实都可以看成是本片的很好的一个注释。在对话之中,法国人表明了自己坚守的理由,理由有二,一是这所庄园是他的祖先开垦的,他的家就是这所庄园。其二是他为了维护“法兰西”的尊严。同时,他对维拉德上校直接戳破美国越战的谎言:越共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支持的,而美国人在这里并没有家园,美国人的战争毫无道理。另外一个隐藏在这段信息背后的是对“1968左派 ”精神的讽刺,法国人讲了一个段子:在奠边府血战的法军拉开手榴弹,掉落下来的是一张纸条:要和平,不要战争。而在整个对话之中,影片使用了大量的正反打告诉我们维拉德并没有认真的听法国人絮絮叨叨,而是同法国寡妇眉来眼去,果然,接下来就是一场带着存在主义色彩的激情戏。在嬉皮士常用的大麻催幻下,维拉德和法国寡妇发生了关系。法国寡妇在这个过程中说出了一句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存在主义宣言的台词:“你还活着,上尉”。
从这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出来,《现代启示录》和他的原文文本《黑暗的心》,从表达内容的层面来说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说《黑暗的心》是对殖民主义辛辣的嘲讽,那么《现代启示录》显然更加侧重揭露资本主义逻辑的谎言:政府对于民众的欺骗。所以说《现代启示录》,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部反战的电影,而是反对越南战争这种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战争。要知道,科波拉曾经参与著名美国主旋律战争电影《巴顿将军》的编剧工作的。
应该说,1979年的这个段落可以说并不是很符合时宜的,因为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是一个中左派当政的时代。虽然激进派在1969年失败了,但是稳健改革的社会党或者工党,成功的执政,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欧洲的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缓和,欧洲走向联合,而殖民地政策也偏向于开明化。
所以说,从国际环境来看,这个段落显然是不讨欧洲观众尤其是左派执政的政治家们的欢心。另一方面,对于国内来说,他的讽刺对比又过于过火,所以在1979年的公映版本中,这个段落才会被删掉。
二.十分钟女权老去
纵观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越南战争可以说算是一个分界线。越战之前的女权运动集中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客观来说,随着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政治,整体而言女权还是一个发展的倾向。而肇始于越南战争的性解放运动则试图从身体上解放女性:女大学生们高呼:“要做爱,不要战争”,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性解放运动对今天美国影响利弊究竟何如,仍旧有很大的争议,不过《阿甘正传》中的珍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偏差的女性样本:她饱受摧残,并且患上了艾滋病。
在《现代启示录》中被删的片段中,也有这么一个长达十分钟的,对女权运动反思的段落:维拉德他们遇到了被击落的“劳军女郎”的飞机。维拉德以几箱燃料的代价给小分队换来了同两位劳军女郎春宵一刻的机会。这段皮肉交易被剪辑的无比新浪潮风格:两对男女主人公在自说自话。性爱是痛苦而绝望的,不仅有小鸟的袭击,更有窗外战友不耐烦的催促。从影片中女郎的叙述之中,我们发现,这些被美军士兵视为天使的女郎,不过是普通的美国少女而已。科波拉使用了拍摄商品般的镜头拍摄这些少女:“花花公子”的商标以及呆滞的,喃喃自语着自己驯化马戏动物的少女镜像。这一切无不在暗示一种物化的主题:在越南,这些美国甜心被当做消费品消费。而这写如狼似虎的美军士兵根本分不清“五月女郎”与“十二月女郎”的象征,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少女和玛丽莲梦露或者莉莉玛莲一样,都仅仅是个欲望的符号而已。看起来男人们渴望着这些少女,其实男人们只是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罢了——这验证了女权主义某种层面上的失败:在完全没有规则的性解放环境下,失去了传统家族价值观保护的女性,将受到更大程度的创伤,而且有被国家机器利用,成为维持社会秩序,化解下层阶级冲动的泄欲工具。
在1979年,性解放这个潘多拉魔盒释放的最大灾难——艾滋病,尚没有完全的显露出来。而历经了八十,九十年代强烈的艾滋病恐慌之后,新世纪的美国开始更加辩证的看待性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的关系。直到这个时候,科波拉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命题仍然没有过时。
三.华氏一九六七
当这部影片的重制版于2001年8月3日在美国重新上映,短短一个月之后,高高矗立的纽约双子塔浓烟滚滚,所有的美国电视台都在重复播放着人们慌乱奔跑的背影,电话里惊恐的问候,以及政客们惊慌失措的神情——九一一时间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美国永恒发展的美梦。而搭配着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好莱坞等美国价值机器也开始调整宣传口径,拍摄《独立日》等影片,让美国总统布什成为全球抗击外星人的领袖。当传媒人平静下来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很多自由都已经被爱国的名义所取缔。一部制作算不上精良的片子《华氏九一一》开始试图揭露真相:所谓恐怖主义的源头,和越战的源头一样,都是资本主义贪婪的产物。
而在一个月前重制的《现代启示录》就像是一个准确的预言,添加了一个科兹与维拉德对话的片段。科兹拿着报纸给维拉德看,尽管当时的越战已经陷入僵局,而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众口一词的表示越南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美国的胜利指日可待。这与影片中所展现的在越南雨林中发霉的美军士兵形成强烈的对比,形成一种对荒诞感,表现了科波拉对于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的讽刺。而这种讽刺,在当时看起来刺眼,在九一一大背景下的2001年却显得格外有先见之明。国家安全与媒体自由,成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传媒业的一个重要命题。最近大火的美剧《新闻编辑室》中,为了新闻自由,新闻业者不得不在商业与政治之间艰难的保持着职业操守。
从对于《现代启示录》两个版本的简单对照,我们大概可以发现美国的自由主义虽然仍旧拥有种种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仍旧是向前发展的。虽然美国并没有国内这种强调意识形态的电影审查制度,但是制片厂体系下的商业文化无时无刻不再束缚着美国电影的价值观表达。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的十年之中,随着高资本推动着的高技术的发展,很少有片商愿意投资到一部库布里克式的反体制影片当中了。马丁▪斯科塞斯在2005年拍过一部《天国王朝》,这部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妖魔化伊斯兰文明,恰恰相反,这部电影展示了中世纪十字军内部的纷争以及借着宗教为名的侵略战争实质。所以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遭遇了重大的修改,整体的艺术水平较导演剪辑版差别十分之大,最终票房惨淡。但同时,这也是一个自媒体发达,互联网终端兴起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影视创作者,会找到合适的渠道,继续着奥利弗▪斯通、科波拉们的事业,将真理之道传承下去,生生不息。
5 ) 关于最后一段(导演评论音轨摘录)
关于刺杀的动机:刺杀行动最开始是一个任务,在漫长的旅途中也充斥着各种材料统计,一切似乎有清晰的脉络可寻。可到最后一刻,动机突然模糊不清,甚至闭而不谈。杀与不杀,在此刻只是为了推动时间前进的行为,是生活得以继续的前提条件,选择的内容没有意义,选择的意义只在于选择这个行为本身。就好比影片最后,新国王在万众臣服的目光中,毅然放下武器,回归现代社会。“放下”还是“不放下”,选择而已:选择“放下”体现了导演反战的主题,那选择“不放下”呢?
“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谈虎集》
6 ) 《现代启示录》:能超越科波拉《教父》的,只有科波拉自己

现代启示录
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编剧:约翰·米利厄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主演:马丁·辛/马龙·白兰度
类型:剧情/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197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科波拉面对满堂的媒体和摄影机,向他们如是描述彼时尚未定版的《现代启示录》:“我的电影并不是一部“票房大片”(Myfilmisnotamovie),它并不是关于越南(战争)的故事,而就是越南本身。我们制作它的方式恰恰就像美国人在越南中所做的:我们在丛林之中;我们有太多的人马,太多的设备,于是一点接一点,我们失去了理智。”
四年以前,科波拉赌上两部《教父》中挣得的名声和雄心,亲自出资,从乔治卢卡斯的手中接过《现代启示录》的剧本,举家前往东南亚,在丛林里度过他的人生中最狂热和幽暗的时光。40年之后,在4K画质已经成为标配的时代,电影经历了公映版,和新世纪初的重生版后,于全世界范围迎来了它的最终剪辑。上海的观众迎接这一部宛若全新的电影之时,我们会再次想起他这一番咄咄逼人的自白,仿佛从冥河涉险归来,这位先知向每一个在文明社会中漫不经心,期待着电影结束后照常生活的观众,传递着地球上隐秘的角落里来自死神的讯息。
帝国喊出“末日就在此刻!(ApocalypseNow)”之后几十年,这部电影对刚刚从病毒围城的环球恐慌中稍许解脱的我们来说,除了是一次对影院归来的庆典之外,是否还承载着另外的意味?越战的阴影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然而在和平时代静坐,沉默或者被信息嗡鸣的时分,战争的碎片时常冷不丁地横亘在我们的双眼之前,却又在几天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科波拉的不安难道只是源于反战吗?如他所言,每次《现代启示录》出现在荧幕上,它的意义就超出了“电影”,这不仅仅因为它在一开场就向我们展示自然在战火面前崩坏时化成的尘埃,或是机械在碾碎肉眼之时无情的轰鸣。它不仅是一场为炫耀战争之虚无而举办的华丽舞会,还是从这一场舞会出发,一件一件剥去身上的首饰,衣着,壮举,肉欲和空话,远至未开化的大陆中心,直到蒙昧深处的逆历史奥德赛。

军官威拉德带着暗杀一个疯子的任务逆流而上(河流-历史),“走进”丛林的深处,正像电影脱胎的小说《黑暗之心》中的主人公所说,“并非前往大陆的中心,而是地球的中心”,其隐文恰是人类于地球史(与“历史”的人类中心相对)的回溯,军官,连同着他所代表的文明——像阿彼察邦的叔叔布米一般——一边念叨着终结,一边“走回”丛林,直到在地球史的另一端,看见了自己的另一张面孔。
”我们优雅地享用我们的正餐,血腥的屠宰厂被精心地隐藏起来”。《现代启示录》正像爱默生这句箴言的图解,在电影里美国人似乎打定主意不再为西方列强虚假的正餐礼仪,和它背后无节制的罪恶盖上华美的裹尸布。逆向奥德赛的途中,屠宰场中哀嚎的也不仅是生灵,还有价值体系,人道,语言,甚至还有历史流逝的错觉,以及一个对神祗的想象。或者说,这些在电影中接连死去的词语其实从来都是一根绳索上的同义词,它们之间的转义支撑起了普世生活的表面,但只有在科波拉的旅程中,这些脆弱的维系在朝彼此接近的同时纷纷快速坍陷,文明的两极(极机械和极原始的)在时间的漩涡里相遇,偶像也在虚无和重建间反复徘徊。
那么,《现代启示录》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它是一场对战争的直接记录,我们在其中看不到英雄,看不到群众,甚至看不到斗争,只有在狂热和虚无边缘交际的混沌。科波拉首先遵循的是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历史放弃把握自身的话语,放弃描摹英雄和史诗,而将记忆的刻印权直接交给了炮火。这代表着在电影的一开始,政治机器的权威就被宣告瓦解,一部去意识形态的战争百科裸露在我们面前,被剥除权力的自我掩护,于是我们得以看清历史糖衣下的真相,得以向“斗争,胜利和幸存者”式的革命词汇反诘:“不,你看,没有英雄,我们都是猪!”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该如何谈论它?科波拉在摄制过程反复修改约翰.米利厄斯(JohnMilius)的剧本,甚至根据自己在梦中见到的异象加拍了影片开头在西贡酒店的段落,又在马龙白兰度最终加入剧组的时候,持续三周每天为他即兴写新的对话,因为连科波拉自己也不能决定电影将走向何方。混乱的种子从运动影像中蔓延到了摄像机的背后,仿佛时间借着镜头又完成了历史的重演,我们必须向自己发问,为什么混乱(chaos)是无所不在的背景?
毫无疑问,镜头下越战的狂热即是美国的狂热,我们难以想象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官,会做出出动十几架直升机空袭只是为了在村庄面前的海面冲浪的决定。但我们同时又该意识到,美国在这里又成了人类现代文明的隐喻,一个灌饱了垃圾食品和蒸汽废料的巨型婴孩,凭着一身铁甲在地平线之内肆虐,需要长年累月地嗅到树叶烧焦的气味来维持自尊心的燃烧,法典和天秤对他似乎不再适用,他的眼中也不再容纳得下另一种生灵的凝视。
媒体的满纸谎言,国内的反战舆论,国外的节节败退,长达四任总统的鏖战,像动物一般原始又未知的敌人,苏联的无形压迫,越战的泥泞是美国人的骄傲在70年代急需破解的题眼,但似乎又是一个再精巧不过的借口,向电影打开进入历史中所有迷宫的窗户。“应当爱你的邻居”——它作为一句规训建立了基督教牧养的西方文明,又作为一面文化旗帜在外邦之地掀起了自中世纪以来的腥风血雨。

一心想着冲浪的中尉Kilgore最终势必是这场战争中的牺牲品。即使被荷尔蒙冲昏了头脑的他不至于丧生在枪口下,他也在胜利即纪律的虚妄中也扭曲了人之为人的准则和资格;如果说虚荣和毁灭欲是两个成正比的矢量的话,他正像一条碰巧爬至人类至高处的蠕虫,看清了脚下一个帝国庞杂如蚁穴的无数工程实际上只是海市蜃楼——因为制约它们的法则在权力的至高处便不再有效——在这里唯一合法的炫耀便是毁灭,他太自然地掌握了这个法则,但却忘记了知道这一真相的他也紧紧地被毁灭跟随。
女武神和直升机的轰鸣里,他的侧颜一面反射出意志的满面红光,一面映照出末日的焰火,仿佛瓦格纳和戈培尔共谋的一场超现实集会。他亲自扮演礼教的刽子手,但是却在膨胀的虚荣里进入另一个谎言,并且将在可见的未来里因着这个谎言死去,以库茨的方式,黑人船长的方式,或者《全金属外壳》中胖子比尔的方式。
这个谎言便是权力的幻觉。如果我们还记得《窃听大阴谋》(TheConversation,1974)中的窃听高手哈里的话,便会想起这个男人对向他耳中源源不断地涌来的秘密是如何地充耳不闻,他又是如何精心地在阻挡这些秘密对他的腐蚀。而在他唯一一次选择相信权力给他的馈赠之时,他才发现自己手上其实不曾有过任何权力,并且因着这次轻信,顷刻间他丧失了所有的自由。《窃听大阴谋》中的讽刺恰恰为《启示录》的混乱提供了动能:权力一旦投入使用,欺骗(谈话男女的阴谋)和受骗(谈话的捏造本质)的机制便开始运行,它不仅要毁掉它的敌人,还要吞没任何为它效力的人。电影的结尾,哈里坐在被扒得稀烂的公寓里吹起了萨克斯,周围是权力扫荡而过留下的废墟。这片废墟紧接着《现代启示录》的开头,科波拉将这片哈里蜗壳式的净土放大了无数倍,于是我们置身在丛林之前,螺旋桨和风扇有如权力鼓起的翅膀,同属于这场正义化的恐怖袭击。

如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电影的开场便是TheDoors高唱的TheEnd。在一场骗局(结尾出库茨向威拉德阅读的报纸新闻)的风暴眼,语言最先失效(录音带中库茨的呓语,暗应《对话》中清晰可辨却正言若反的约定),接着是人的面孔(死亡扑克,围观兔女郎的群众),与此同时是帝国的错觉(法兰西殖民地中的夕阳),最后是时间的流逝(混乱的重复,上游逐渐凝滞的时间)。权力即是一个矛盾体,一面不断制造话语和秩序,一面以其自身的荒谬和暴戾承认着秩序的虚无,如果说历史(被权力书写的)是河流中威拉德途径的驿站的话,那一次在河岸上未经历史(权力)许可的停留,便是文明不经意间踏入非历史的失足——大厨被丛林中跳出的老虎吓得嚎啕大哭,因为他从未距离历史如此遥远,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件意象,如此栩栩如生地同时昭示了生和死,而且在生死之间扯开一条一念之差的裂缝。
这一刻我们突然对战争的真相恍然大悟,它是历史朝向非历史的脱轨,是权力按捺不住自身涌动的虚无,朝向虚无发起的攻击:虚无从这个撞击的破口向我们喷涌而出,我们以血肉之躯面对丛林中射出的匿名之箭。非历史的真相是一片嗡鸣的海洋,无意义的生命,它漫没有语言,因此没有主客之分,也没有词语和想象的割裂,但是却漫布在意识和物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历史对它恐惧,于是在这片汪洋上耕种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田地:骗局和遗忘,前者造了一张弥天大网,其形式是自我对话,后者随时洗去网上所有的沙,利用人类短暂且谬误百出的记忆,其形式是修正历史。(库茨读给威拉德听的报纸)
在《现代启示录》中,战争是一个和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截然相反的隐喻,隐喻一切撞入秩序中、或者在秩序的进展中无意间孕育的无秩序,通过将电影书写成战争本身,科波拉让我们直接身处于非历史当中,在这片被掩埋的土壤上,生和死各占一半领地,军舰驶过的迷雾和丛林,象征的正是荣格在《红书》中所阐释的终极意义,它是意象和力量的统一,融合了交替而生的意义和无意义。
可是在历史中只有意义,只有庞杂的因果链条制造的生之假象,它要么英雄化了死,要么将死视为道德或者生物上的必然,通过英雄化将生命变得永垂不朽,通过必然性将理性置于虚无之上,再次暗示了秩序的永存。意义是历史挣扎求索的目标,然而对于非历史来说,它只是一个阶段,或者一个子类型(subtype)。空虚是历史戴上无数重面具尽力掩饰的本质,然而对于非历史,空虚则是它存在的形式,因为万事在其中永远正在发生,正在消解,但从未定型,从未充盈。我们不该说“死是生的结束”,草率地以生定义死,而应该说“死是生的背景”,就像说河流是船的背景,以此扩大生的定义。

于是我们可以解答为什么在科波拉的电影中,战争的每一个侧面:空袭,浪花,椰林,浮桥,灯火,血肉,平民,都只是像费里尼片中千奇百怪的面孔一样飘过,它们不显得惨烈,甚至在虚幻中异常壮观:因为这是通向非历史的路、道和桥梁,是理智(威拉德)转变成荒淫(库茨)的过程,起点是文明的死亡,终点是意志疲惫不堪的沉默,我们途径风景,它们在死亡的壁画上显得匀称且虔诚。《现代启示录》便是这样一次寻找,它不朝向外部某一件失落的珍宝或者臆想的传说,而更像月球寻找自己的暗面。威拉德的长途跋涉,其实又只不过是从远古以来就决定背向深渊的人类一次艰难的转身,这个动作是如此微小,但却要求他重新怀着雅各和上帝摔跤时的激情和恐惧。
但这个对个体来说犹如移山的任务,对群体来讲却轻如鸿毛。个体需要突破文明沉重的地壳,但是文明想要跃入自毁的深井,只需将历史的一叶障目从眼前挪去(正如科波拉所做的),或者始终被作为人类保护罩的历史转而变为人类的敌人,后者在20世纪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中反复上演。人文荒芜(horror)和道德灾难(moralterror),库茨上校的两位好友,又或者是两位主人,即是非历史自身(丛林),和历史中未能成功抑制的非历史(罪恶)之显影(embodiment)。它既存在于外部,也存在于人性之中。文明正像荒原中拔地而起的一幢高楼,它庆祝自己的奇迹,竖立自己的标杆和偶像,在它使自己的尖顶离地面越来越远的时候,它似乎逐渐遗忘了自己仍然扎根并始终属于这片荒原。相信秩序会像雕塑一般永恒,它患上了骄傲病,认定自己的崛起就意味着这片荒原的消逝,不曾发现荒芜在源源不断地从建筑内部向外生长。过高的理想会成为最毒的刀刃,我们立刻可以想到的例子便是共产主义的历史:荒原张开血盆大口,等着仍然向上攀升的危楼倾覆的一天。这便是圣经中告诉我们“(末日的)时间近了”的缘由,它所警示的并非一个由神决定的终结点,而是由人的姿态决定的,与时间流逝无关的结局。
权力制造了文明的囚笼和时间的漩涡,但这一墙之隔内,错误的并非历史的存在,而是历史试着一手遮天,让一个族类相信它便是世界的全貌,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失去和非历史和谐相处的机会。库茨上校口中的越共比起美国大兵,更擅长在恐惧和野蛮中生活,他们对伦理了然于心,同时又和死亡同样亲近,善于爱,也善于破坏和杀戮,因为在这个残缺的世界里,完整的爱也意味着心甘情愿准备去破坏。因此当我们将爱和和平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也就预兆着自己将更容易失去它们,因为我们必然无力抵抗突如其来的恐怖,只能在它的意象前俯伏投降,正像库茨上尉被它咬至空心的躯体。
我们的时代正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犬儒主义,一面是秩序堆起的骗局,在一正一反的错乱中,双双阻止着信仰的重新诞生。威拉德必须要杀死库茨,因为人类必须要超越自身的死亡欲继续生活,但人类又不能忘记死亡,于是库茨像图腾动物一般在一派狂欢的仪式中被夺去了生命,从这一刻开始他才真正被当成神祗纪念。在库茨的身上,在科波拉的造神运动中,我们看到信仰诞生之初最原始的形式:它并不像其所暗示的那样关乎永生,而是代表着人类与死亡,与无秩序和解的第一步。反而是撕碎了信仰的世界,更像一个遗忘死亡的永恒之城,在这里才居住着口口声声地听信民祈祷,赐风赐雨的上帝。无独有偶,在疫情初临的全球封锁,和重现阴霾的国际局势中,我们似乎发现了自己完全失去和恐惧共处一室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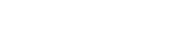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科波拉:「《教父》採用的是古典風格,每個鏡頭就像場景整體結構的一塊磚頭,而場景就成為一堵漂亮磚牆般的設計。Gordon Willis認為,一個鏡頭不該包羅萬有,否則就沒有理由切換到另一個鏡頭了。另一方面,在《現代啟示錄》裡,Vittorio Storaro則期望鏡頭像移動的筆桿,從一個影像元素滑動到令一元素。最終我向蘇菲亞和我自己解釋,鏡頭可以像一個詞語(前者)…….但也可以像一個句子(後者)。」(《未來的電影》)
癫狂的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魔幻主义交织一起,呈现了《现代启示录》这般末世审判的景象。科波拉书写了现代的Apocalypse,并超越了普通战争片的层次,讲述了泯灭人格如何拥抱野蛮和原始的寓言,反战之上是对人性的剖析,为极端人格划出了走向野蛮的结局。电影语言一流。但个人没有太喜欢。
前半部几乎是某种肆无忌惮的炫耀,而到达了彼岸的王国后,一切都彻底凝滞,证明了它是一部为了虚无的战争拍摄的虚无影片。
看完身心俱疲
正片200分钟,花絮100分钟。音乐和音效是超级无敌强大地!超现实的战争片~摇滚&古典~
好看到爆,焰火礼花燃烧弹,血肉横飞迷幻药,法国人的教训美国人的挽歌。沿湄公河而上,一路上的人性扭曲和战争疯狂叫人震撼。文明和道德在这里并无栖身之地,冲浪摇滚乐也不是。三个半小时并无困意(尾声的大面积阴影略困),极度难得,赞美上海影城一厅东方巨幕,非常亮,秒杀电影资料馆
威拉德最后在柬埔寨科茨的王国中被当地人捉住,见到了科茨。然而,科茨竟欲求一死,叫威拉德将这里炸为平地
不是因为长,我建议慎看的原因在于——看完你会怀疑人类文明与世界的意义,如果没有足够的哲学素质,它实在是令人身心俱疲的。科波拉强烈的悲观主义浸染于此。我倒不认为难以理解,只是看完太难受。即使是在说教,这种说教又相当的令人——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电影堪称伟大,!9.1
【B+】令人头皮发麻的音效和配乐,登峰造极夸张到不行的布光,越南战争看起来就像嗑了药一样迷幻。
在《故事》一书中作者认为本片是离题而失败的..我则认为此片是荒谬且失望的..看的时候还很年轻,但已经能了解到那种说教味道..现在再回去想想看,会觉得还是库布里克的战争三部曲更能打动我心.战争是人类的本性呢,这就和讨论”何以为人“这问题一般不可让人那么容易就得到明确的答案呢..三星
战争和人性的交响曲,配乐太棒。前半段是神作,后半段爱不起来。
说教味太重,太冗长,意图太明显,科波拉就差直接把想法写成论文了。
三小时的布道式催眠。所谓战争,不过是在烟雾、炮弹、鲜血、污泥、雨水中的狂浪梦游,不存在谋略深浅或是意志强弱,只有如嗑药一般的诱惑力与吞噬感。死亡是摆脱梦魇的唯一出路,但噩梦不会停止,还会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这才是当代文明得以运行的不二法则。科波拉用一种独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第一强国的铺张奢华之力,完成了电影史上最昂贵的一场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忒长了,几次都没坚持到看完
节奏分明的三段叙事,一部关于战争的狂人日记,难得看到科波拉如此意乱情迷。感觉“蛇之拥抱”和“迷失Z城”都要减星了...“Horror!Horror!”
非常赞同罗杰伊伯特对本片所持的观点:现代文明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栖息在大自然饥饿的血盆大口之上,一不小心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吞下去。幸福的生活在这种脆弱面前只是日复一日的缓刑。与其说它描绘的是战争,不如说是战争如何揭露了我们永远也不愿发现的真相。| 大银幕重温,震撼到被封印在座椅上。(SIFF,4K,天山-虹桥艺术中心,2020.7.30)
战争题材总是让人倍感深重。。。
只能说从东方文化的观点看 导演没必要那么罗嗦
看了一半就忍不住来打5星啊
逆流向上找到你,只是为了亲身体验你缘何成为了你。真正的绝境没有出口,将所有人都死死困住。不讲原则的毁灭,似乎也能成为美丽的源泉,慈悲心虚伪无用,我见得越多就越讨厌谎言。因离婚而抑郁的你,可否向我的儿子传个话啊,再出世也不能免俗。其实是科波拉写给自己的情书,自恋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