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九十年代初的西部小城,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张小雷(孔惟一 饰)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没有作业的暑假。然而这个自由的,炎热的夏天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红火热烈,更多是平常反复的家庭生活和大把闲工夫。恰逢那一年国家开始实施国有单位转型,铁饭碗被打破,张小雷父亲(张晨 饰)的单位也受到改革冲击,他们生活的家属院 里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影响着。孩子们整日百无聊赖,而看似平静的大人们,心却像烈日炙烤着那般燥热。张小雷就那么静静的耗着,感受着身边隐隐发生的一切。直到父亲为了生活同其他人远走他乡,家里只剩下了母子俩,张小雷才着实感觉到时间过去了,生活不一样了。立秋那天夜里,张小雷家的昙花在院子里悄然开放,像是意味着什么……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变身契约天才一族1990谣言沉默的证人(国语版)超感神探第六季英雄(国语版)真假学园6放逐戈壁母亲有道理的爱情灰姑娘药剂师黑百合小区恶搞之家第三季线,画出的我花样年华2000黑死病 上一念天堂终极密码战外星人入侵爱情账单夺娶柏林龙卷风莱克伍德新夏威夷神探第四季巨商金万德红点杀机
长篇影评
1 ) 终于轮到80后来怀自己的旧了
首发于《环球荧幕》3月刊。
推荐这本优秀的电影杂志
纸质刊物生存不易,请大家多多支持,且珍惜!

小男孩作为男主角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大雄”而不是“胖虎”,这部《八月》也一样,孔惟一饰演的小雷外表羸弱,不声不响,骨子里却全是闷骚的小意志:崇拜着大院古惑仔、双截棍从不离身、看不惯就棒打老师、追着坏同学满院儿跑……印象最深的是考试失败,他理直气壮地去厨房对着沮丧的妈妈喊:“莫以成败论英雄”。影片正是通过这些细节,一点点将小雷那种不谙世事又极力成长的耿直boy形象塑造出来,可爱而亲切,似乎在遥望记忆对岸小小的自己。
导演张大磊用了非常冒险的手法:散文式的叙事,以小雷的视角,将那些改变社会的大事讲述得不动声色。这种正常人心电图式的节奏一旦没有把人抓住,看的人很可能难以入戏,因为只有一步步让每个角色都成为你“认识的人”,才能跟片中的人物一起在这黑白的光影中生活一次。所以说张大磊很是大胆,这种“去戏剧性”让它几乎注定在院线成为小众。
然而,并不是把各种段子随便拼凑一下就是“散文式”,它同样需要铺垫和设计,需要稳健的节奏、柔软而丰富的镜头语言,还有一点点打动人的小心思。看似是个“小片”其实有大量的人物需要塑造,场景也多,小空间内的调度复杂,绝对超过一般“小片”的体量。在小雷看来这个八月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很多改变社会的“大事”却在他不经意间暗自风起云涌:长辈的生老病死、为了升学而“走后门”、大厂改制、爸妈买断工龄、铁饭碗下海、好莱坞大片闯入中国……那些被说成“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是将生活片段生生截取几帧,加以巧妙组合,这种结构恰恰印证了我们记忆本身的模式——琐碎而模糊,而一旦联系在一起又往往让人惊一下。
导演拍这部电影就像把我没有能力做的事做了出来。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没有刻意去弄一个要么跌宕起伏、要么耸人听闻的主线故事出来,也没有让“情怀”“怀旧”沦为符号式的卖点,感谢他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讲记忆、讲时代。
2 ) 小时候不明白的事,看完都想起来了 [猫]
本文部分发表于《上海电视》4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
《八月》给喜欢艺术片的影迷带来的冲击,没有《路边野餐》那么大,后者以一个超级长镜头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探讨人生的种种遗憾和情感,情节设置相当精巧。这两部,我都在影院看了两遍。
但《八月》未必不梦幻,不诗意,不以镜头语言说话,它淡淡地带观众去往另一个方向——恢复我们的某种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记忆,基本被导演张大磊浓缩在短短一个月里。这种处理,很容易产生把时空线索刻意装进一个罐头的效果,参见无数引用非典和张国荣之死的国产青春烂片。这一层,张大磊做得勉强自然。
这也给电影造成弊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人,如何明白,国企改制给下岗工人带来的瞬间绝望?个体户在当时是个什么地位?严打是什么?以《亡命天涯》开启的每年十部分账大片如何震动了电影市场?
95后00后怎么看他们出生前的社会状态?
没有背景知识的外国人能否看懂?
过来人,如我,甚至比我离片中经验更近的那些大厂子弟,看完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和启发?
本片用了11岁小雷的视角,又不只如此,还父亲的视角、上帝视角,最后时近时远、疏离朦胧地讲述了小孩不明白、过来人一看就懂的社会状态,它甚至没有中心情节。说到底,它是需要观众主观参与的电影,用意识去缝补一场场戏之间的联系。
怎么说呢?这就像我们普通人去看《魔兽》,只是看了个故事单薄的奇幻片,游戏玩家去看呢,就是看着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游戏角色变成真人走来走去,角色讲的笑话,我们都听不太懂,玩家懂,角色的社会背景、江湖地位、情感关系,我们不会注意,玩家却能从一个小细节看出导演用心。《蝙蝠侠大战超人》同理。
《八月》因为生活化,很真实,所以观众可以不费脑筋地看导演铺画册,一页一页,即便不去主观缝补剧情,这个电影时空也是成立的。但是看完之后呢?
既然是画册,《八月》大概还是影像出彩。此片风格略似做起梦来的杨德昌,但没有杨德昌那种犀利冷静的态度,杨的电影基本不会给我们对现实发梦的机会。
我很喜欢《八月》里警察追捕不良青年三哥那场戏。近景里的小雷看着远处虚景里警车边的人渐渐跑近,与他擦身而过,是三哥,小雷也跟着跑起来,先是听到三哥呼叫的声音,接着远远看着他被逮捕的全程,此处的视觉语言正贴合孩子懵懂迷惑的视角。
有人说本片看不出张大磊在莫斯科学过电影。但小雷梦中的水上倒影,河溪边因黑白影像而显得格外明亮灿烂的小树,明明沾染了塔可夫斯基的风格。
梦境多少与现实相连,越到后来越模糊界限,也避免了复制小学生作文式生硬的转场交代。
比如,德彪西的音乐渐强,小雷在被邻居小姐姐亲脸的瞬间醒来,此刻小姐姐正在用小提琴拉曲。
比如,他说想上重点中学三中,是因为校服帅还能配上三哥那样的漂亮皮带,一向宠他的爸爸气得把他丢路边,自己骑车飞奔回家。于是他梦到爸爸带他在草间寻觅,不知道在寻觅什么,最后找到了蛐蛐,爷俩还一起吃西瓜,他讨好地说“爸,我不去三中了。”
这是儿童臆想中的困惑、解答与和解,在梦中完成。
爸爸坐车去远方做场工,切入同伴搞联谊的场景,再切回车上。这个场景里出现了那位每天早晨站在阳台上唱美声还常常即兴喊诗的大叔,因为他后来又出场,在小雷母子看昙花的时候喊诗,所以我们判断那场联谊不是未来场景的插入,它像是在车上的一个梦,这也可能是男人对未知明天的茫然想象。
激起这场车上飘飞的,是《你在他乡还好吗?》。这让我们赫然想起,那几年最流行的,原来都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大哥大哥你好吗?”“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你那里下雪了吗?”词曲虽流俗但质朴真挚。
再想想今天外头唱的都是些啥,时代印记,民风人貌,都蕴藏在流行乐里。
父亲大概是全片塑造得最立体最有血肉的角色。
他总嚷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却不得不随他瞧不起的韩主任,离开熟悉的家园,放下剪辑的本事,去跑拍摄现场。揾食不易。
他看到韩主任也会赔笑,也任凭儿子追打韩主任的儿子。韩主任在楼下地图炮乱骂,他就暴躁紧张。他连见老丈人,都要站起来,像跟领导汇报工作。
他嘴里说国企改制是让人凭真本事吃饭,内心却焦虑不安。只能喝喝酒,一遍遍观看《出租车司机》尤其是那句“Who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to?”
最激烈,也只是半夜抡空拳中发泄一番。
他惩罚了儿子,晚上又不好意思地过去劝儿子快睡觉,既心疼又愧疚。
他们看绝症梗爱情片《遭遇激情》,儿子看不懂睡着了,他却看得泪流满面。
男人喜欢的浪漫都很残酷,是生离死别。
这种真实,大抵体现了张大磊对身为剪辑师的父亲怀有的深爱与敬意。
讲真,看完这部片,我一直沉浸在写自己童年往事的兴致中。唤醒,也许就是这样一部艺术片的意义吧。
---------------------------------------------------------
请关注我的公众号 “树屋钓月亮”。
3 ) 《八月》:1990年代的文化记忆
本文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热点评论”栏目。亦见于公号“映画台湾”2017年6月3日同名推送。有删改。
文丨黄豆豆 / 瓜子酱
德国学者阿斯曼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论,他的著作《文化记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解释文明发展规律。
在涉及到文化记忆的媒体时,他归总有文字类和仪式类两部分,前者包括书面文本和书籍,后者包括语言和口承文学在内。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的话,文化记忆的具体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
在国内,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较为著名的文化记忆作品,她用文字和书籍作为媒介,选择了11位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刘索拉、崔健、甘阳、李陀、田壮壮等)进行访谈。
在该书的序言中,她写道:
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进入90年代后,一些在80年代开始的东西又被搁置了。庆幸的是,9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发展。经济、资讯、新一代人的成长心态……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2]
正是由于时代的快速转型和变化,再加上新旧媒介的更迭,以及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的记忆也正面临着一系列疑问:我们需要记忆什么?我们该如何来记忆?在记忆之中我们又应该怎样处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更年轻的张大磊,则用影像作为媒介,记录了他成长经历的、如查建英所言的“发生着重大变化”的90年代。《八月》既是他个人自传式的记忆,也是他父辈的集体记忆,更是以群体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记忆。
一、晓雷的八月:自传、目光与感知的伦理
《八月》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方小城(呼和浩特),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晓雷迎来无所事事的漫长暑假,并目睹了国企改制背景下的一系列家庭变故。在被宣布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时,官方给出的介绍是:
《八月》是一部气质突出的电影。全片以黑白影像呈现,透过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旁观大人的世界。然而它不只是一个男孩的成长,更是对人情世故、体制变革,以及时代记忆的回眸与反思。
男孩晓雷无疑是这部电影的线索与中轴。一方面他的名字对应着《八月》导演张大磊,给电影增加了浓厚的自传色彩和作者感。小升初的升学压力、萌发的性意识、一直挂在脖子上的双节棍,以及最后与昙花的合影等,或多或少带着张大磊的童年投射,但也不必完全求真。而影片的名字“八月”也意指对孩童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暑假,强调的是晓雷的感知。另一方面,晓雷是电影中所有非线性叙事的旁观者。外婆卧病在床日渐衰弱;晓雷等待升学,父母托关系把他送进三中;制片厂改革后,父亲一番挣扎最终外出跟组挣钱;家中的昙花在一个夏夜悄然绽放……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晓雷并没有参与全部,但一直作为一个隐形的视点存在。有时候,电影坦白地展示出晓雷的目光,如落魄的父亲在深夜朝空气打拳那场戏,观众是跟随晓雷的眼神目睹的。跟随着晓雷的目光,观众还目睹母亲生闷气到不想做饭,大家长一本正经地训话,崇拜敬慕的哥哥被抓,以及电影剪辑室里被废弃的胶片……这分明提示我们,晓雷是这个八月的旁观者、经历者和感受者,电影在通过其视线凸显他的感知。而当导演张大磊躲在摄影机后拍摄这场戏时,整个空间中就出现了两台摄影机,或两个记录者:晓雷和张大磊。晓雷是借助回忆和想象而被还原的当事者,张大磊则是来自未来的再审视。这样的双重叙事使得电影的自传色彩显得更为迷人,即观众被告知:他们不仅在观看90年代,还在观看张大磊回忆与思索90年代这一过程。
这样的视角处理就使得《八月》所表现的1990年代场景一直在接受晓雷/张大磊的注视,造成不在场的“在场”。于是,《八月》的孩子视角既不像《城南旧事》(1983)及小英子,以全程的参与来获得关注、推动情节发展;也不像《一一》(2000)及张洋洋,因有限的儿童视角而未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洋洋更像是一个意蕴深长的象征)。
晓雷所感知的是全景的氛围,它不仅仅是家族的嬗变,更是时代的大场景与小细节。张大磊曾回忆2008年8月的一次回乡:
吃过午饭,我坐在那个躺椅上,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不像是当下那么嘈杂的声音,它很细微,但是它让周遭的环境显得很静,时间变得特别慢。[3]
这是张大磊下决心拍《八月》的重要起源,而他确实把这样的听觉环境恰如其分地还原了:电视新闻播报声、邻人在胡同巷弄中的聊天嬉闹声、救护车经过的鸣声、“磨剪子,戗菜刀”的叫卖声……这种听觉的真实,再现了晓雷静谧、无聊而又琐屑的小升初暑假,甚至给人一种置身南方的错觉(导演本身没有赋予电影在时间和地域上的确定性)。加之摄影师吕松野在黑白影像中拍摄出惊人的层次感,更显小城的静与慢。对于近年来《冬》(2015)、《塔洛》(2015)等电影对黑白影像的使用,王红卫以双关的“黑白的故意”概括,既含导演刻意为之之意,也取“故去”、“故往”、“故国”、“故事”等过往之意。[4]
其中后者是与张大磊向90年代行注目礼相吻合的。而在《八月》中,黑白影像更凸显出梦一般的质地,夹杂着晓雷年少的幻想,代表着导演不刻意求真实、模糊含混的美学取向。这是张大磊对待回忆的态度,落脚于晓雷无聊、孤独的八月幻梦里。幻梦甚至有层次,电影中一场戏拍晓雷的梦(目睹杀羊、被倾慕的女孩亲吻等),其空旷辽远的质感大大有别于黑白色的市井。梦醒,晓雷望向楼对面的邻家女孩。可见这到底是强调晓雷自身意识的90年代。
因此,《八月》获得了在童年题材电影中一个独特的位置。孩童作为一种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身份,常被电影设置成关键、隐秘情节的目睹者,如《城南旧事》、《冬冬的假期》(1984)等,都是孩童的“知晓”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孩童自身的感知力反倒是其次了。
《童年往事》(1985)、《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则又设置了太过激烈的环境裂变,孩童的感知被无限放大了。
在《八月》中,在孩子升学、父亲谋生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平凡命题里,张大磊用一种举重若轻的自传式回忆书写带来一种全新的感知的伦理。他以回望的姿态强调孩童的感知,这既是一种来自未来的自省,又带着含糊的疏离;晓雷既因其永在的目光成为时代气氛的引领者,又恰当地因孩童身份而撤退,使得电影制片厂等实在的背景在寻常巷陌中隐去。因为晓雷仍是一个导演所熟悉的成长于1990年代初的“80后”,有其自身投射而又非彻底的记忆搬运。这依旧不同于《一一》中带着杨德昌丰富意图与隐喻的男孩洋洋,他的旁观反倒有了来自成人世界的预知感而成为一种神话。
二、父亲的八月:理想、现实与重拾的尊严
尽管晓雷是《八月》的线索与中轴,但片中的父亲无疑才是电影真正的主角。片尾的字幕“谨以此片献给我们的父辈”明确点出,致敬父辈才是《八月》的真正主题。电影中晓雷的父亲是一名电影剪辑师,在下岗潮刚来临时坚信自己可以凭本事吃饭,始终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去社交、求人,甚至也坚信孩子不一定要上重点中学才有希望。他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锯掉墩布的棍子给小雷做双截棍、在影院里看《遭遇激情》(1990)泪流满面、跟岳父讨论国家政策时信心满满……
这是父辈的理想主义。凭借着片中的电影元素,《八月》获得了与电影史直接沟通对话的可能,父亲的理想主义更是因其电影剪辑师的身份而染上些许迷影色彩。片中在电影院前后共出现了《爷儿俩开歌厅》(1992)、《遭遇激情》、《亡命天涯》(The Fugitive,1993)三部电影。其中《爷儿俩开歌厅》是1992年陈佩斯自导自演的“二子”系列电影的一部,而陈佩斯正是中国最早吃螃蟹的“电影个体户”,砸碎了旧电影厂的体制,这与《八月》的内蒙电影制片厂改制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亡命天涯》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海外分账大片,《八月》里展示的当时15元的高票价意味着父子俩再也蹭不到电影了。[5]
这种和电影史的互文,更与父亲的形象相映照,带来一种象征的意味:计划经济结束,国产片独占影院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像父亲一样的国营厂工人能否从破碎陈腐的旧体制中走出来,我们在片中还无法得知。片中有一个画面是父亲带着晓雷一起端详电影胶片,这一幕使人联想起电影《天堂天影院》(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中代际之间迷影精神的传承。
“以戏写戏”本应该使电影和人物染上神圣的迷影光环,但导演的处理却十分克制隐忍,在对电影元素的偶然提及以外,总以平凡生活的细节刻画处理制片厂人群。如导演细密地还原记忆中的物体系:鸡啄米闹钟、摇头电风扇、长毛狗玩具、双卡录音机……又设置了90年代普通城镇小区的平凡人物:晓雷对面楼房的“梦中情人”、电影院的售票大妈、父亲的死对头韩胖子、游泳馆的登记员、中学的招生老师……在这样低到尘埃里的时代气氛下,我们似乎都忘了这是一场关于制片厂改制的大潮,而小男孩的父亲还怀有一身电影剪辑的本事。这样的处理同样给父亲的理想主义蒙上一层阴影。
作为一个颇具理想情怀的“艺术工作者”,父亲对待晓雷的教育也是如此。他帮晓雷制作双节棍,对晓雷是否一定要上重点中学不做过多的要求。这不禁令人想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父亲形象,同样时运不济,却又基于一种充满人格魅力的评价方式对孩子的教育报以宽容。而这样的一种宽容,若放在父子俩各自人生“一退一进”的形势中,就显得更为难得。再若与时代大潮相结合,则突显出个人命运在现实中的无力感。时势的变化、家庭的责任,以及个人的能力最终还是让他坐上了去外地剧组当场工的大巴。而为了让小雷上重点中学,他跟着去请客应酬,交昂贵的赞助费;电影末尾,穿着军大衣的父亲在草原的风中跑动,顾不上跟家人好好说上一段话,手持摄影的镜头因为摇晃而抖动,正像向生活妥协后辛劳奔波的父亲。正如李健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值得一提的是,当电影元素终于在这一刻赤裸裸地被表现出来时,这一段在大草原上拍摄的画面令人惊颤地与《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形成互文。
阿巴斯的戏中拍戏是对电影真实性的挑战,他以一种消解幻象的方式制造间离以提示观众的思考;而张大磊在这一片段中终于回归到观众所熟识的彩色,同样是否定了前一串黑白故事的真实性,提醒我们黑白色的回忆只是梦境,或带着导演本人对90年代似是而非的想象(尽管他对气氛的重现足够真实而引人动容),而父亲为家庭做出牺牲、奔波劳苦才是唯一的真实。据导演自述,这一段后期补拍的戏,是为了让电影不仅仅展现“父亲的妥协”和“美好的逝去”,而还有“父亲到底在做什么”的内容。[3]这是父辈的现实,也是子辈对父辈的致敬。
于是,电影的目的显然不是在国企改制背景下去刻画人们的惶然与痛苦,或以成功学的视角对他们加以成败或对错的判断。现实中导演张大磊的父亲成为了一位知名的电影剪辑师,并站在金马奖的舞台上作为制片人之一与张大磊一同领奖,即证明了这部自传式电影意不在此。与之相反,《八月》是在还原与重拾时代重压下父辈们作为人的尊严。父亲唯一一次责骂晓雷,是认为晓雷觉得“三中校服好看”太没出息,可见其在妥协后依旧保有自尊。在厂子转型时期,晓雷的爸爸邀请同样失意的一群哥们一起喝酒,几个大老爷们喝到兴起突然齐声唱歌,迸发出所有的尊严与苦恼,颇令人动容。看完《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后,父亲对着空气拳打脚踢,这一幕道尽一个男人的愤怒与无奈。
在这几处喷薄出恣肆情绪的段落里,电影少见地放下了它矜持的恬淡,以一种外扩的诗意的形式为父亲吟诵,告诉观众这是父亲无奈牺牲而又不失尊严的八月。
三、90年代的八月:代际、秩序与共时的脉搏
20世纪90年代开始登上银幕和舞台是近几年出现的文化现象。近两年的《黑处有什么》(2015)、《少年巴比伦》(2015)均将镜头对准90年代的大工厂,而2017年年初上映的《乘风破浪》(2017)则以穿越的方式轻巧地寻回90年代。
更早还有《钢的琴》(2010)、《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等电影刻画90年代的痛点。旧宿舍、老国营厂、老社区……
当这一系列记忆中似乎熟识而又着实古旧的符号登陆大银幕,我们就被告知: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或21世纪初)已经开始频频成为被追忆的对象。
在这之前,20世纪80年代才是那个被中国电影史频繁提及的时代,是一段从“文革”的阴影走出而迎来新生的历史,它浪漫而富有激情。从封闭走向开放后,那个时代盛行的文化热所承载的是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等宏大叙事的信仰和渴望。与之相应地,《本命年》(1990)、《长大成人》(1997)、《那山那人那狗》(1999)、《青红》(2005)、《颐和园》(2006)、《爱情的牙齿》(2006)等一批电影均将个人的命运与心迹和时代大潮结合起来,急切地反思着80年代的历史进程。
而当21世纪临近,90年代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氛围。前半期的短短几年拥有其复杂性、独特性和阵痛感,市场经济经过一番政治震荡而最终确立,普通民众经历了国企改制而挣扎犹疑地在旧工厂和新的商业大潮中游走。后半期,人们的思考方式发生收缩式的转换而朝向了个体的实利,尤其是在90年代末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中,以冯小刚《甲方乙方》等系列电影为代表的贺岁档电影开始出现,世纪末的都市图景开始以一种狂欢化和奇观式的方式被呈现,这一段历史似乎并没有被严肃、诚恳地言说。
可以说,在被剥离了浪漫与宏大的情况下,90年代一直没有以追忆的方式在大银幕上被凭吊和表达。直到现在,当中国电影市场已经井喷成年度票房457.12亿元、年度观影人次超13亿的量级时(2016年数据)[6],这一段岁月才终于站在被回望的位置上重新现世,其背后的根源是文化权力的更迭。
毫无疑问,每个人有其所属的时代。如果按照苏珊·桑塔格早在1996年所说的,电影已经因为电影迷恋(Cinephile)的结束而死亡,那么我们其实根本无法从根源上领略法国新浪潮的魅力,我们与那个时代注定失之交臂。而随着谢飞导演拥有了一个豆瓣账号,老一辈的话事人也不得不适应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当在90年代还是稚童的“80后”逐渐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的时候,他们中就必然出现掌握媒介话筒的文化塑形者。华语电影也是如此,“80后”逐渐成为大银幕的话事人,也成为电影院观众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信息爆炸、社会压力巨大的今天,足够触动他们的恰恰是记忆中的90年代初。对成长于内蒙古制片厂家属院里的张大磊来说,小学毕业那一年,父辈们“空闲时间忽然多了”,“常结伴去外地找活干”,[7]这就是他执导之初急于表达的个体经验,而他拍摄的《八月》就这样精准地击中了90年代国企改制的时代节点。韩毓海曾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来阐释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所有的文化秩序都是特定的和相对的,新旧文化秩序之间的常面临阵痛的转轨。[8]
张大磊与其《八月》呈现了一个反例,他以回忆的方式去再现90年代并致敬父辈,实际上是以一种柔和的姿态帮助旧文化秩序进行转轨。金马奖以鼓励新人的姿态将最佳剧情片颁给《八月》,其实是一种对这种柔和姿态的回报;在《八月》公映前,陈道明以一句“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力挺该片,同样应证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这仍是因为《八月》对时代气氛的精准描摹。戏外,电影因为其在First影展、金马奖舞台的存在感而使“时代脉搏与个人命运共振”类似的主题在公映前就先入为主、深入人心。但其实,在国企改制的背景下,电影并没有以一种哀悼的姿态去展现时代带给父辈们的痛苦,90年代的下岗潮也还远远没有席卷到那个制片厂的家属院。电影只以一种恬淡忧伤的调子,由男孩晓雷引领我们去重温90年代的琐屑真实,制片厂的相关元素其实是淡化的。父亲或低头求人,或失意喝酒,或外出干活,都是普通人的离合悲欢,都至少代表生活还没被逼上绝境,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韩胖子那样朝着新时代迎头而上,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时代重压下穷困潦倒。这样一种忧郁而不失希望的对待时代的态度是击中当下“80后”人群的关键。同为刻画劳动人民,《八月》不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那样以开放式结尾去提示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思考,它只关注共时层面下的气氛与情状,也因此而容易陷入流于时代标本的困境。
在电影末段父亲已然缺席的日子里,院中的昙花在一个八月的夜晚悄然开放,晓雷在盛开的昙花前俯下身来,微笑着与它合影,将电影重新投回到生活中去。这个看似象征意味太过明显的设置,其实本是导演张大磊真实的个体经验。电影的本名原来也叫《昙花》,但后来主创出于“不想让它有太明确的形式感”的原因,而将影片更名为《八月》。[9]但不管怎样,这样一个隐喻式的结尾给了我们巨大的阐释空间。这既是一个时代底下的普通的喜悦,却也是一个时代的注解。张大磊曾这样向家人解释自己决定拍电影时的感悟:
那年夏天的昙花忽然开了,虽然开很短,但它还会再开的!
90年代的逝去和它在当下的重现就是如此。尽管秩序的演变已然发生,但之所以我们能够在二十年后的现在再度把握其共时的脉搏,只是因为我们在时间长河中恰好仍处于与90年代合影的阶段。
阿斯曼夫妇认为,“文化记忆”既区别于历史书写又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统”。记忆之所以不同于历史,是因为它是以群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意即,它从来都是有倾向性的,以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对于个体来说,回忆的过程大多数时是随机/随时发生的,服从个体心理机制的一般规则;但是在集体和制度性的层面上,回忆过程则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或称遗忘政策的控制。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产,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
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到人工的文化记忆的过渡却可能产生问题,因为其中包含着回忆的扭曲、缩减和工具化的危险。这样的偏狭和僵化只能通过公共的跟踪批评、反思和讨论才能减少其负面影响[10]。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张大磊的《八月》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已逐渐过渡到集体的文化记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浪漫化、缩减或偏差的可能,但它能够引发经历过90年代的观众的集体共鸣,说明它在完成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目标是成功的。
注释:
[1]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2):239.
[2]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三联书店,2006:序言.
[3]蜉蝣.导演张大磊:《八月》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EB/OL].//movie.douban.com/review/8431128/,2017-03-22.
[4]朱津京@BC.《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何炼成,满满干货奉上[EB/OL].http://mp.weixin.qq.com/s/G528MB9bG2KVPhosB7wIjQ,2017-04-19.
[5]落山风.是的,我一点不伤心地泪奔了好多次[EB/OL].http://mp.weixin.qq.com/s/6vmPt1g7A1BQp0DrJX89TQ,2017-03-25.
[6]参见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457.12亿元[EB/OL].http://www.gapp.gov.cn/sapprft/contents/6582/312058.shtml,2017-01-03.
[7]刘珏欣.张大磊:九朵昙花开在安静的1994[EB/OL].http://mp.weixin.qq.com/s/nd4jnmu4EPCdSYi_Nym6Fw,2017-04-01.
[8]韩毓海.1954《红楼梦》讨论再回首[EB/OL].http://www.m4.cn/space/2012-03/1156530.shtml,2017-03-19.
[9]少年王,参无见.《八月》:电影、父亲和我[EB/OL].//mp.weixin.qq.com/s/vTvthA9sGY6Ybrr5EC2Cdw,2017-03-16.
[10]阿莱曼·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记忆到公共演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76.
4 ) 一部电影的「年代感」应该怎么营造?
一直以来特别想吐槽,今天忍不住出来胡说八道一下,如今热衷于拍摄年代戏的编导们,其实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如何真正地让观众「入戏」。
所谓「年代感」其实指的是「回忆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在脑海中过一遍久远的记忆——那些陈旧的记忆对比鲜活的记忆,其质感的差别是怎样的?
因此,仅仅在服化道上下功夫抑或者是老歌大串烧,最多不过架空复刻一个虚无缥缈的外壳形式,在剪辑与影像本体上下功夫才是正道。《八月》之所以不能够获得我的共情,很大一部分程度在于其景深效果使用的失误。换言之,是张大磊作为导演摄制思路的失误:他误用了2010年后影视创作者们普遍形成的数字化的拍摄思维,去表现了二十年前中国社会剧变下个体的困顿。
那么「数字化的拍摄思维」要做何理解呢?电影是一门及其依赖机器的商品/艺术,从早年的「西洋镜」到「摄影枪」;从梅里埃黑白胶片手工上色到红绿染印法的里程碑;再飞速发展到如今几近普及的5DIII、DJI OSMO、BMCC乃至Red One等数码设备,机器作为拍摄工具的更新总是在不断丰富和推动电影的拍摄方式和表现形式,因此造成了一个现象:特定年代的电影作品,其主体、对象、形式、语法都与那个年代所具备的机器条件不谋而合。
这就促成了一个年代区间内诞生的电影作品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恰恰就是「年代感」的核心体现。而由于不同地域经济条件与电影工业的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其相同年代区间内的「年代感」也因此在题材和形式上各有不同。
从这个结论出发,一个近年来恰如其分还原出「年代感」的正面案例,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典型表现是在影片中不同的年代段落里,使用了不同的、对应年代常见的画幅比例。其他更多不显山露水的手法还包括但不限于:
一、色彩。


同为90年代,《山河故人》的画面在色相与饱和度上存在着一定的色偏和失真,为的是对应上90年代那个以胶卷和磁带为主的影像模式。而《乘风破浪》中浓郁如泼墨般的色彩,好看归好看、浪漫归浪漫,但很显然与真正90年代影像特征有着较大的出入,缺乏说服力。就像影片穿越的内容一样,构建的是一座完全架空的海市蜃楼。而《八月》中占据大部分的黑白画面,无论从对比度、高光和阴影部分展现出的宽容度与画面的锐度,都是清一色典型的当代数字画面。也许张大磊在后期的阶段应该请调色师多拉拉画面曲线什么的,像《山河故人》第二部分那样,把画面做出早年拍摄器材感光原件并不出众的那种泛白、低像素的质感。


就不拿九十年代时代背景的《乘风破浪》和同年代背景的《山河故人》比,就和韩寒自己的前作《后会无期》(时代背景为当代)比,相同的机位,相同的景别,相同的桥段,看得出差别吗?
二、景深。
之所以专门把景深拉出来讲是因为这是《八月》最让我出戏的元素。有过比较多拍摄经验的同行应该都有类似的感触:如前文所述,自从电影从胶片时代逐步过渡到数码时代,机器所能调动的轻便性和本身性能的突飞猛进已经基本上改变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思维。以往的光圈和胶片的感光度不足以支撑机器通过虚实来「压缩」画面内容使画面美观、干净不杂乱。因此回顾国产2000年前的电影,画面的景深范围往往都能够保持在起码十米以内,相比如今动辄长焦、微距、大光圈设备拍摄出的浅景深镜头泛滥,那个年代更加强调拍摄环境的光线、距离、布景和时机与画面的构图、平衡、韵律是重中之重。《八月》的镜头显然在这些部分显然欠了一些考虑。(后来从曾和张大磊当面交流过这一问题的友邻那儿得知,《八月》因为经费有限选择的主要拍摄场景是正在拆迁,拍摄的前后过程中环境变化较为显著,不少桥段不得已使用与九十年代不符的浅景深以规避环境变化造成的跳戏)

当然因为思路问题造成的出戏在景深方面只是一部分,从韦斯·安德森在国内影响力大增之后,正平面镜头、舞台视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国产电影中。这是有悖于强调画面「纵深」的传统的。同样是两侧遮挡的场景,对比《八月》与其致敬的《悲情城市》,空间的层次感差距颇大。


三、运动。
和景深问题有着同样的原因,设备机器的更新改变着镜头本身与镜头内运动的形式。旧时的国产影视作品往往习惯于通过出入画与纵深来突出运动感,我印象最深的是86版《西游记》片头还是片尾的最后一个固定机位镜头:摄影师将机器放置在地上处理成略微仰角拍摄的角度,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从摄影机上方跨过走向远方,这时画面内容是六小龄童从画框上方入画随后从前景走向后景,而接下来另外的师徒三人一马亦步亦趋分别从左、右、上方依次入画从前景走向后景,画面运动在视觉上非常丰富。
如果说以上的运动方式是属于旧时代的,那么新时代的运动方式显然发生在机器愈发便携化之后。手持拍摄即是一个典型代表,大陆开始大量有意识、成体系地使用晃动手持镜头形成风格的代表人物当属娄烨。娄烨习惯将手持与主观镜头相结合,制造角色内心的飘忽和悸动。这其实是最切合运动镜头拍法的思路:注意运动的物体甚于静止的物体属于人的生理本能,来源于进化过程中对外界信号的反馈心理。娄烨用手持的方式将运动-心理的关系勾连起来,完成影像的内容表意。而包括《八月》在内的如今多数国产电影镜头中的运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废素材,就像后来模仿冯小刚在电影《大腕》里植入广告的那些人,植入的广告真的只剩下了广告的作用,而不是有机地与其他道具一起,共同起到明确/隐喻主旨的作用。
包括《侠女》中间竹林对阵那一场戏,胡金铨在画面中安置竹竿、树叶、岩石作为前景,将人物安置在中景、大环境作为后景,拍摄对象尽管始终被运动的镜头捕捉在画面内,但多层次的空间反复遮、露、挡、显、藏、现人物,依然保留有强烈的视觉趣味性。



遗憾的是,不论是哪一种年代的运动,都没看见张大磊在《八月》中地道地使用的痕迹。从还原「年代感」的要求上退一步回来说,《八月》连基本的视觉趣味都稍显匮乏。
四、帧率。
这部分与《八月》这部电影无关。只是基于「从影像本身出发营造『年代感』」这一问题衍生出来的探讨。帧率的变动同样是基于电影机器的进步。从早期的8帧/秒到16帧/秒到通行于世的24帧/秒,再到《霍比特人》48帧/秒与《半场无战事》120帧/秒的探索,每一次转变,背后都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不正印证了「年代」这一概念么?
五、镜头。
《爱乐之城》为了向古典好莱坞致敬,表现出歌舞片黄金时代复古的风格,达米安·沙泽勒特地选用了在1953至1967年间主流的变形宽银幕镜头拍摄。此外,片中诸多场景的镜头都被刻意地一镜到底,减少镜头之间切换的频率,是达米安·沙泽勒在拍摄技法上对黄金时代歌舞片的另一种「回归」。

5 ) 八月
电影中有三处关于皮带的情节,我很喜欢。第一处是小雷目睹三哥街头勒索学生皮带时羡慕的目光;第二处是小雷说要去八中的理由是因为校服帅,有皮带,惹恼父亲;第三处则是父亲离家工作打拼前,在儿子睡觉时悄悄在桌椅上摆了一个新腰带。用手遮挡了一下台灯的灯光,怕吵醒儿子。那一刻,很感人,我可以说这个细节出现的恰到好处,将父爱展现的淋漓尽致。早上母亲拉着还未睡醒的儿子去送父亲赶车,我相信看到这里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这种送别的场景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过,留住好时光,期待再相见。从这一刻起,小男孩扛起了家里的更多责任,他明白许多,也成长了许多。
朴实,简单,不绚丽却不失内涵,是我对这部影片的整体感受,很不错的一部电影,值得一看。
6 ) 如果你也有一个不善表达的父亲,如果你也有一段不被看好的童年,请一定看看《八月》。
我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长大的孩子,这部电影对我的意义,可能大过很多人。 电影中的台球桌,标放,露天泳池,就在我家南边,走路不超过五分钟。路边叫卖的西瓜,年年都有,不过我们都拿勺子吃。还有那一大家子人,哦,包括抢钱的大孩子,都离我太近太近,仿佛就是昨天,他们还都在我身边。 我看完电影一路哭回了学校,然后哭唧唧的给我爸打了个电话,给他买了电影票让他晚上去看,他有点被我吓到了,毕竟我长大后就没跟他这么哭过。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我那不靠谱的爸爸带我去看的《拯救大兵瑞恩》,当时的我只有五岁,开场不到十分钟我就被枪炮声吓得大哭,我爸只能带着我出了电影院。 我爸是一名摄影师,他经历了片中父亲所经历的改革,他像片中的父亲一样一看电视就睡着,一样不愿“低下他高昂的头颅”。厂子改制后,他开过照相馆,卖过挂历,最后还是奔波在剧组。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小时候的我嘱咐第二天要上组离开的爸爸“走之前一定要叫醒我”,但当我早上醒来时,他都已经带着行李出发了。离家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还记得有一次他回来留了络腮胡,我被吓的嚎啕大哭,他被爷爷赶去刮了胡子才来见我。 我爸妈在我很小就离婚了,所以家里不像片中有妈妈做饭,我爸在我小时候又不会做饭,我一从奶奶家回去我们俩人就每天下馆子,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吃遍了家周围所有的小饭馆。我爸也带我在标放门口用那些岌岌可危的球桌打台球,在路边摊吃羊肉串和田螺。 我们电影厂的孩子大多数都有个“坏孩子”的标签,因为我们像电影里的“三儿”,爱和人打架,像“小雷”,每天疯玩不爱学习,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不许你和他们玩”“你可别像他一样”。我们院儿的孩子,一半在三中,一半在三十五。我和我的发小们也经常在标放看不买票的电影,在厂院里打闹,爬到院里的大榆树上摘榆钱,在院里打水仗,捉迷藏,数数我们都认识了二十多年了,我们还和彼此在一起,那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他们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们之中的很多人现在都在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让我们来拍我们自己的故事。 看完《八月》,我觉得我的童年,第一次被认可了,就好像有人告诉十岁时被嫌弃的我:“你这样,也是可以的,最然会走些弯路。”。 我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爸这么多年不向厂子妥协,不愿拿那几万块的买断工资,为什么不愿“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我从前觉得他执拗,不听劝,甚至不可理喻。却从来没试着去理解过他,他绝对不是个完美的爸爸,他倔,脾气差说话直,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他永远支持我任性的决定,给我选择自己路的权利,这是多少孩子不曾拥有的。 那老师,如果你不想低下你高昂的头颅,就永远别低下,无论这决定是对是错,我都陪你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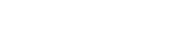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小城是会变的,分账片再也没法免票入场、画海报的被迫转行刻字、剪辑师低下高贵的头颅离家当场记;小城又是不变的,升学仍需金钱和关系、亲人终会放下芥蒂、夏天依旧那么燥热。声声吆喝带回九十年代,大环境下人心惶惶,小雷爸对着空气无物之阵地挥拳,却无处对抗与挣扎。穿上三中校服,八月好似昙花。
看到后面才知道故事发生地在内蒙,但是拍的感觉就跟南方一样,90年代的复古感,跟自己经历的一样,“我们还是出去下馆子吧” 简单一句家常话,真是好久违。结局致敬的段落跟去年的《告别》如出一辙,减分。
之前看过,标记一下,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声音做的非常棒,用耳朵听仿佛就能回到那个过去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响,当下的孩子以后拍他们的童年,肯定就不是我们那时候的声响了,只需要竖起耳朵,这片子就是满满的怀旧气息,声音这点做的很加分。
真挚的一场回溯。进入封存着懵懂模糊的夏秋之交,动用比《黑处》更多的时代符号却不显堆砌感,在绵密的日常细节中带出压抑伤感的时代挽歌。气韵依仗台湾新浪潮,但更重要的是导演唤起温暖的记忆与亲情,给这场编织的诗意划上情感的立足点,尤其临行前进屋遮灯光那场戏,感人至深。2016华语年度最佳。
三星半,导演对90年代初那段回忆的重现还是很有味道的,甚至带出了我的各种记忆。国营工厂时代的结束,不但是那个年代的成年人,对那时的孩子其实影响也很大。影片碎片式的记忆了很多童年的往事,情节并没有非常集中,而是很松散的汇编在一起。故意隐去很多关键情节,却没有影响剧情进展,这个不错。
80后献给自己童年记忆的散文诗,对于自己父母一辈年轻时的回望。它其实并不那么优异,有些过于散淡。对于那个年代社会转型时对人心的触动,很多都没能表达清楚。但很少有人去这样描述那个时代。这算是一次不太一样的回望角度。
这种全程孩童视角但始终格格不入的设定显然从牯岭街来的,但有视角还得有情感啊,杨德昌那种愤世嫉俗,真是学不来的。其实有不少值得发展的角色和方向但最终还是停留在这无变化的视角,于是只剩下当时的文艺中年和现在的文艺青年的顾影自怜。贩卖情怀的电影真的有点看腻味了...
用程蝶衣的话说,这个导演是懂戏(电影语言)的。几个镜头值回票价,不堆砌符号,小演员好。
优点是对生活的尊重及捕捉视听形象的执着;缺点是编、导、演掌控的青涩。依我的观点FIRST不应颗粒无收,金马又评价过高。但评奖从来是具体评委们在特点地点、时间的表达,无可厚非。新导演要稳得住,坚持该坚持的,提高该提高处,迅速地投入下一个实践。记住,头三部作品是你一生创作历程的关键。
写给父辈失意的诗,昙花会开的,我们可能不会了。哭了三次,鸡皮疙瘩一次。
这几年first里边最喜欢的一部,致敬父辈迷影元素,儿时的记忆正如这样散碎模糊,琐事也像昙花一样开在了心里。国营制片厂改革由主任改叫经理想起了诸多那个时代的变迁,不只是儿童视角,最后我也从他爸爸看到了自己。塔洛摄影的黑白影像,提名的出色声效设计让观影仿佛回到那个夏天。导演映后见面场,祝去金马多拿奖。
现实题材容易遇到的局限,就是需要相同的生活环境才能引发的共鸣。真正可以跨越文化障碍的电影,首先是有艺术性,其次是普世的情感,人类共有的悲喜剧。这个有点拍小了,充满琐碎的矛盾与混乱,没有抓住任何清晰的脉络。导演希望保留儿童记忆中的世界,但毕竟这已经经过情感和时间的重构了。
小孩看待体制和家庭变迁,不想搞清楚为什么,也不想批判谁,就是觉得这段日子挺美好,有点忧伤。长镜头配忧伤的旋律很有艺术范儿。P.S.经导演本人确认,片中的“老云”说的就是蒙古族著名导演塞夫。
比起侯孝贤可能更像杨德昌加上[压路机和小提琴]的老塔,但就算语言是借来的,记忆和情感却是极为真挚的(不仅是内植,我甚至觉得这部影片会有一种反向的内植哦)。把内蒙厂还原成国企,并选择了那个关键的时刻,这简直是电影史的神来之笔。影片声音设计极为有想法。等上映了一定要去影院再刷一遍。
比较像学生作品。几个比较明显的瑕疵:小孩这个角色如果全部拿掉整部电影也是成立,九十年代初转制改革对工人带来的冲击力是肯定有伤到骨肉的痛感,影片中始终弥漫的却是感伤化的小情小调,这是视野问题也是缺乏社会历史洞察力的表现。一拍艺术片就用黑白片的方法实在也是看疲倦了。2.5
文艺电影四大俗,彩色结尾黑白片,片名不肯马上出,固定机位长镜头,怀旧金曲串串烧,八月四俗此俱全~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输送FIRST标配。以小孩去写大人的小大人视点,最后变成了突兀存在(一度跳到了「钢的琴」等),泛滥着文青影青的20世纪末感伤,也生吞了小孩子应有的童真稚气。情怀大过天,也不能掩饰影片本身的无力。喜爱看「出租车司机」的孩子他爸分明就是真人版桃姐,这个可以加分
结尾父亲的剧组拍的是《八月》就厉害了。
小演员让我想到少年张震,导演学特吕弗的意味很明显。从“路边野餐”到“八月”,我们的青年导演似乎总不懂得怎么把剧本写得高于生活,他们以为只要把生活的枝桠剪下一段就可以直接插进电影的花瓶。——这叫偷懒。
想起黑处有什么,但黑处很外行,让人尴尬,而八月非常好。八月有自己的气质,节奏,品位。有一股文艺气息,看得过程非常舒服。那些情节和对话虽然没有做到特别精致和自然,但在同期的比较中已经能完胜了。希望看到更多这种气质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