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东京湾岸区连续发生杀人事件,被害者皆为溺死,警方的调查毫无进展。警官吉冈(役所广司饰)在事发现场找到一枚纽扣,回家后却发现自己的外衣正好掉了一粒同样的扣子。其他的蛛丝马迹也表明与自己有关,他开始怀疑自己就是凶手。为此吉冈苦恼万分,而恋人春江(小西真奈美饰)却表现得十分冷淡。重返凶案现场的吉冈,听到了诡异可怕的声音,并见到一名红衣女子(叶月里绪奈饰)。女子告诉吉冈,15年前,她曾为他所爱并被他亲手杀死。 吉冈独自来到精神医生高木(小田切让饰)那里求助,多年的老同事宫地(伊原刚志饰)也开始怀疑吉冈,他徘徊在友情和职责之间难以做出抉择。吉冈的生活渐被击碎,他打开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秘密……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边城小镇2006创业吧,骚年只是孩子恋爱小说小飞侠1995先发制人惊心小说无穷之路4:一带一路海军来了撕开你的伤口暮海情深放射治疗室第2季美狄亚斯杨三姐告状百变艾琳第一季初次见面,我爱你 はじめまして、愛しています。循环恋爱中马尔科姆的一家第一季伊波拉病毒神秘之火鬼太监传送法低压槽:欲望之城女人的历史
长篇影评
1 ) 好电影推荐
这部片子非常奇特,先从静静地凝望开始,就像伯格曼自己眼中所见的,对每一样东西都专注地看上一会儿,背景很简单,每一样东西仿佛都是艺术品一般独立地摆放着,每一个特写之中没有别的杂物。
然后故事开始慢慢地发展,每一个细节都真切细致地表达出来,就像 个小孩在观察着大人的表情一样。
再后来,伯格曼就开始讨论一些古怪的话题,镜头转入人心的深处了,从表面一下子滑进去。
我真是喜欢极了这种内向人的世界。
导演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自从他的表面华丽精致的精头多了些后,他忽然开始讲故事,情节匪思所夷。不过他讲的节奏也是不慌不忙的,每次一个片段,之间没什么过渡。而观众的心却在不断受着传统的冲击、冲击,同时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动。
2 ) 她比我们都坚定
为了回忆一下剧情,我去豆瓣找找影评,发现伯格曼的这部彩色片人气还真是高,影评一抓一大把,扫了一下,很多写的很好的。不过,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要说的,也只是我自己的伯格曼。一部打动人心的电影,总是能让观众看得到自己的。
故事情节很简单,主要人物是四个女人,三姐妹,Agnes,Karin,Maria,还有女仆Anna,Agnes得了重病,快要死了,几个姐妹们都来看他,温情脉脉的姐妹情谊之下,又暗藏着冷酷和绝望。也许只有女仆Anna是最简单的,让我们感觉到一丝温暖,只有她才是真正最简单的爱着Agnes的。里面最著名的镜头就是Anna赤裸着上身怀抱着Agnes,这是这部以暖色调为主的电影里面,唯一能真正让人感到温暖的。
关于里面的感情,很多时候让人琢磨不透,又让人着迷。有点让人想到晚期的贝多芬,刚用明朗的弦乐抚摸着你的内心,却又转眼之间又用刺耳的和弦让你感觉到自己有多么傻。姐妹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我也不知道,也不敢说,Karin始终在保护着自己,似乎永远都看不透她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感情?而且感情奔放的时候有着莎士比亚式的激情,而又转眼换成马基雅维利式的冷酷。还有Maria,Maria看起来稍微有点生气,但是内心里,也很难说她有多少真正的怜悯。Karin在痛苦之中,用碎玻璃插入自己的阴道,让人感到令人心悸的无声的痛苦。可是Maria呢?只有她在被痛骂的时候的面部表情,才让人感觉到这是个活生生的人。
再回忆一下影片中牧师所说的,她比我们都坚定。荒诞和冷酷之中,爱与被爱者,总是太让人伤心。Karin的封闭和孤傲,还有Maria的自私和冷漠,这些都是外在的,但是究竟在内心里,Agnes又有多少坚定呢,她不也是一直在寻求着姐妹们的爱么?再坚定的人也总得在这样的冰冷里寻找安慰吧。
最终的结尾非常耐人寻味,Agnes的日记之中,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载,在那洒满阳光的亭台之下,姐妹们和睦地游玩着,那时的Agnes的健康还很好,阳光下的,让人想到莫奈笔下撑着阳伞的女人。如果这个镜头放在开头,这会让人感到如此幸福和美丽,然而在这所有的冷酷的故事之后,再来温习这样的一个镜头,总让人感觉到有点无力。Agnes真的那么坚定么?还是伯格曼自己写出来的寓言?伯格曼不停地摇摆,不停地询问,不停地回答自己,可最后也让人太过无语。
3 ) 我不是你的母亲
电影《呼喊与细语》中艾格尼丝回忆她的母亲:“尽管母亲已经过世二十多年了,我几乎每天还是会想念她。以前,她常到公园里去寻求宁静和孤寂,而我会远远跟着她,偷偷地看着她。因为我爱她,爱到骨子里,爱到嫉妒。我爱她的温柔、美丽和充满活力,爱她的绝代风华。但她也有冷漠无情的一面,甚至是玩乐般的残酷,但我还是忍不住为她感到难过,而现在我长大了,更能理解她了,多希望我能再次见到她,我想告诉她,我理解她的沉闷和急躁。我理解她的渴望和孤独。母亲总在主显节前夕举办一个派对,奥尔加阿姨会带来他的神灯和童话故事,我总是感到被冷落,我很害怕。当母亲以她那轻快而不耐烦的方式,对我说话时,我不知所措,但玛利亚和母亲总是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是如此相像,我满是嫉妒,想知道她们在笑什么。每个人都玩得很欢乐,很尽兴,只是我无法参与其中。我记得另外一次,那是个秋天,我站在窗帘后面偷偷地看她,她坐在红色客厅里,穿着她的白裙子,她就那么坐着,低着头,手放在桌子上。突然她看到了我,用温柔的嗓音叫我过去,我迟疑地走到她面前,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批评我,但是她的眼神充满了悲伤,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把手放在她的脸颊上,在那一刻,我们非常亲近。”

伯格曼在自传《魔灯》中写道:“今天,我伏在童年时的照片上,用放大镜仔细端详母亲的面容,我试图重温那长久流逝的情感。是的,我爱她。照片上的她非常迷人,宽宽的前额上覆盖着浓密的棕发,鹅蛋形脸庞细腻柔美,性感的双唇温和善良,浓黑姣好的睫毛下,双眸温存恬静,两手娇小而有力。我四岁的心灵里充满了像狗一样的忠诚。然而,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单纯。我的忠诚使他烦恼和焦躁。我亲近的表示和强烈的情感爆发困扰着她。她经常用冷漠讥讽的话语赶我走,我只能怀着愤恨和失望的心情去哭泣。她和哥哥的关系则简单得多,她一直帮他抵御父亲,父亲总是用严厉的手段教育他,残暴的鞭打就是一个实证。我慢慢地认识到,用温顺与狂怒交替往复地表达我的爱慕之情没有丝毫效果。因此,我不久便开始试着以自己的行为去逗她高兴,去迎合她的兴趣。病痛能立即引起她的同情心。让自己浸泡在永无休止的病痛中,这的确是一条痛苦却真正能引起母亲关怀和体贴的捷径。另一方面,由于母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我的把戏很快就会被戳穿,并当众受到惩罚。用另一种好的办法讨好她,结果更糟糕。我知道我的母亲不能忍受冷漠和心不在焉,她把这些作为她自己的武器。我也学着抑制住激情,开始做一种独特的游戏,游戏最初的花招是傲慢和一种带着冷漠的彬彬有礼。我虽然不记得我做了什么,但是爱会使得一个人善于进取,我很快成功地在敏感和自尊的结合中发现了有趣的东西。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从来没有机会揭穿自己的游戏,扔掉假面具,放纵自己,投入彼此关心的怀抱。”

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曾为她的女儿弗莉达写过一首《晨歌》,里面有一段是: “我不是你的母亲/一如乌云洒下一面镜子映照自己缓缓/消逝于风的摆布。”
1963年2月11日清晨六点,普拉斯抛下睡梦中的两个幼儿,在自家住宅开瓦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起身上楼,到孩子们的房间,在桌上放了一盘奶油面包和两杯牛奶,怕他们自起床后到打工女孩到来之前会觉得肚子饿。然后,她下楼,走进厨房,用毛巾尽可能地将门窗的缝隙封住,打开烤箱,将头伸了进去,打开瓦斯。
而在西尔维亚·普拉斯自杀四十一年后,曾经被抛下的睡梦中的幼儿之一,她的女儿弗莉达还原了她母亲诗集《精灵》的全貌并为此作序,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女儿对母亲的爱与理解:“我不想看到人们以宛如‘她得奖了’的方式来纪念我母亲的死。我希望她生的事实受到颂扬和肯定:她曾经存在,曾经竭尽所能地生活,曾经快乐和悲伤,苦恼和狂喜,并且曾经生下我和我的弟弟。我认为我母亲在工作时是独特非凡的,在与纠缠其一生的忧郁症奋战时是勇敢的。她善用每一次的情感经验,仿佛那是可以拼制成一件华服的小布块;对感受到的事物,她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在能够驾驭那些混乱骚动的情感时,他就能够集中心力,有效地发挥她惊人的诗歌能量。然而,我母亲自杀当下的极度痛楚却被陌生人接管了,被他们占有,并加以重塑。《精灵》诗作集结成册象征我拥有了我的母亲,却让父亲蒙受更多的诽谤。这好比她诗歌能量的黏土被占据之后,再以之捏制出对我母亲的不同说法,捏造者的目的只为了投射自己的想法,他们仿佛以为可以占有我真真正正的母亲,一个在他们心中已然失去自我原貌的女人。我看到《拉撒路夫人》和《爹地》这样的诗一次又一次地被剖析,我母亲写作它们的当下被套用到她整个人生,整个个体,仿佛它们是她所有经验的总和。”

你的母亲用冷漠背叛你,而你为何仍旧迷恋她?
因为无论如何,她是一位美丽优雅让人无法拒绝的女人。
4 ) 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瞬间的美好与永恒的地狱
影片伊始,阿格尼斯在痛苦中醒转,看着熟睡的玛丽微笑,在日记中写下:“星期一清晨,我在痛苦之中,我的姐妹们,还有安娜轮流照顾着我。”是为三人和解I。
故事接着推进。阿格尼斯在嗅花中展开了对母亲的回忆:母亲同玛丽亲密和我却疏离,我常常处于烦躁、厌倦与孤独之中。唯有在某一绝望与悲伤的时刻,我与母亲互相抚摸着靠近,终于感觉到了亲近。可以看出,我与母亲的关系是普遍的分离与瞬间的和解,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剧中三姐妹关系的最终走向。是以我们定序列为与母分离I和与母和解I。
随后是玛丽与医生的偷情与回忆,在丈夫自杀的扭动与玛丽的拒绝施救中回忆终止。深夜,阿格尼斯病重,卡琳和玛丽被安娜叫醒。阿格尼斯彻夜痛苦地喘息着,直到清晨才好转。她微笑着醒来,其余三人其乐融融地服侍,为其洗澡、喝水、梳头、念书。是为三人和解II。
然而阿格尼斯最终还是病情加重而死去,牧师作祷,影片随后进入了卡琳的回忆。在“全是谎言,全都是”反复言语中她将玻璃碎片刺入下体,并将鲜血展现给丈夫。回忆终止,玛丽前来寻求过分恶化的姐妹关系的和解,而卡琳只是拒绝、不安。是为二人分离I。
玛丽再度劝说,卡琳局促地捧起阿格尼斯留下的日记阅读:“某一天,我收到了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团结、友谊、亲密、慈爱,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美好。”三人一度在回忆和日记中达成了和解,我们定为三人和解III,却是虚幻、短暂与过去的。
玛丽企图触碰卡琳,先是遭其拒绝;再度触碰,没有拒绝。玛丽轻柔地抚摸,卡琳哭泣着,当她想要亲吻时卡琳大叫着抗拒:“持续不断的折磨,就好像在地狱里一样。我不能呼吸,真是罪过。”两人这一系列的进退迎拒最终还是导向了分离的局面,是为二人分离II。
由此电影已过大半,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分离、和解序列的发展:
与母分离I
第一组:三人和解I→与母和解I→三人和解II
第二组:二人分离I→三人和解III→二人分离II
第一组序列是和解包着分离,第二组是分离包着和解。影片发展至此给我们留下了悬念,家人之间的情感最终导向何端?但同时可以预见,之前每一次的和解不是出现在日记、回忆中就是暂时、不祥的。
重新冷静下来的卡琳和玛丽对坐着商讨财产和去向问题。短暂的平静后两人继续对峙。卡琳说自己常常想到自杀,没有人爱、安慰、帮助,嘲讽着玛丽的轻浮、空洞与虚伪,说什么也逃不过我。然而在大声的呼喊中她祈求冲出房间的玛丽的原谅。在萨拉班德的乐声中两人互相抚摸着、无声地倾吐,看似达成了和解(二人和解I)。然而被有意消音的对话和萨拉班德让这来之不易的和解显得诡异。
影片的高潮出现于阿格尼斯的“复活”。哭泣的阿格尼斯幽幽地诉说着:“我不能睡过去、不能离开你们”,却遭到了卡琳和玛丽的相继拒绝。卡琳残忍地说出了“我并不爱你”,玛丽先是抚摸,却在阿格尼斯的拥抱中恐惧着逃离,唯有安娜敞开衣襟,宛如圣母怜子般再一次怀抱着阿格尼斯。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对于这一情节的浓重的刻画,以示三姐妹的关系不可逆转地分崩离析,绝望、令人窒息地再无修复可能。是为三人分离I。
影片末尾,全家人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般围坐在一起,冷漠地讨论房产和安娜的遣散。离开之时,卡琳想要确认同玛丽的关系,却再一次遭遇了她的漫不经心和轻蔑的冷笑,是以伴随着这一家族人际和生活的再度步入正轨,两人的关系又恢复常态。二人分离III可谓是宿命般的结局。
镜头随后转向阅读日记的安娜。阿格尼斯描绘了一幅四人在一起的和谐场景:“我想牢牢抓住这一时刻...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可以期盼了,这就是幸福。现在我能享受这完美的时光,享受好几分钟。我深深感谢我的生活,它给予了我这么多。”只能出现在回忆中的美好和团结再度出现,是为三人和解IV,影片结束。我们不应忽视这一情节的作用,作为电影的最终幕,尽管是回忆,它也是曾经一度存在、发生过的美好,并必将常常被安娜回忆起,而在将来可能被再度经历的和解。
电影最后一部分的序列如下:
二人和解I→三人分离I→二人分离III→三人和解IV
和解和分离的局面各占一半,召示着这样的主题:瞬间的美好与永恒的地狱。犹如萨特所言,即便生来便是地狱和无意义,我们亦可以在寻求自由和解脱的过程中确认自身的价值。我想引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中的著名论断:“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呼喊与细语》是一出现代的古希腊悲剧,伯格曼借此探讨了存在主义的议题,其强烈的“卡塔西斯”作用召示着这并非哲学而是艺术。相应的还有宗教隐喻、绘画等等元素共同作用,在此不提。
5 ) 伯格曼电影笔记之《呼喊与细语》:1971年4月20日
2,安格尼斯维系着其他女人们的关系,电影一开场就表现了这点,及至她死去,她们试图重新建立另一种关系,失败了,失败得很惨烈。伯格曼丝毫不想将电影抽象化,四个女人以各自的肉体为精神的一种反映,每一具肉体清晰地指向一个方向。
这是好手段,不晦涩,不玩弄观众。
3,有两个插叙,一个是玛利亚与医生及丈夫的纠葛,一个是卡琳与丈夫的纠葛,两段都是往事,伯格曼将对前者的叙述安插在安格尼斯死亡之前,将后者安插在其死后。,为什么放在哪里呢?
同质的自私和冷漠,玛利亚呈现为一种渴望与利用的姿态,卡琳是拒绝与伤害的姿态。
伯格曼定是从大自己四岁的哥哥身上获得灵感来刻画卡琳的丈夫。
4,结尾放置的那光明和谐是伯格曼的一个把戏。它确实汩溺人心,可从故事的时间顺序看,两姐妹来看望安格尼斯是在电影开头之先,三人重聚古堡中,才开始了彼此痛苦折磨之旅。
5,为什么同时使用伯格曼的旁白和安格尼斯的独白?
,6,裙裾的窸窣声,钟表嘀嗒声,人的低语声,像空气一样充盈于空间里,启发甚大。
7,伯格曼依旧沿用了他从前的一些技巧,比如特写运动镜头,在脸与脸之间像拉弓一样的运动着,张力毕现。
8,电影必须要直接诉诸感官,必须要直接诉诸感官,要直接诉诸感官,直接诉诸感官,诉诸感官,感官。
这电影很稠。没有一个人能毫发无伤地从电影里走出来。
盈耳催落繁钟,撞眼几重满红,垂死欲勉残灯,此世何必更生,每夜长为愁府,无言难起情冷,畴昔至再至三,与君共是由衷。
6 ) 伯格曼《呼喊与细语》:当弥留之际
一般来说红色太过霸道,只能作为衬托的存在,但在此片中伯格曼却将高饱和度的大红色大胆地铺满了整个背景,而让人物身穿黑白灰无彩系的服装。这种反套路式的美术设计,很明显是有象征含义在其中了,丝毫不限制红色的扩张,使背景色完完全全以大片大片的留白面积压过了人物,营造出了浓烈、压抑的氛围。艾格尼丝的白色服装形容了苍白的病态,罗琳的黑色则是隐喻了内心的冰冷(罗琳的镜头也经常用较远的景别来表现,因为她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闭心情)。

同时,灯光也是视觉语言的主角之一,电影中有不少镜头都运用了伦勃朗光影法,以烛光照明与自然光作为主要布光手段,加强了人物面光的明暗影调,三角光极大丰富了画面内的可塑性,看起来十分具有文艺复兴时期油画的质感。安娜接受艾格尼丝时,镜头极具张力,打光十分有油画质感,人物姿态则致敬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成名作《圣母怜子》。

在剧情的发展中,镜头经常以快速推进至人物特写,以此来强调主观镜头的情绪效果。交代时间的钟表镜头加速着节奏,是重要的组成元素。当镜头逐渐推到近景或特写时,背景那大片的红色留白起到了强化人物主体的作用,没有任何杂物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甚至连浅焦摄影都不需要。人物的眼神打破了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对话,使语言台词更有了跨越维度的穿透力。时不时出现的伦勃朗三角光又添加了人物的舞台戏剧感,并进一步丰富了画面。所以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属实有大师水平,塞满了镜头语音的信息。

故事线很简单,中途用红色全屏留白作为过渡转场,把现在与过去两条时间线拼接起来。而主题“呼喊与细语”表达得比较晦涩,应该指的是每个主要角色心中的内在心理状态。在艾格尼丝弥留之际,每个姐妹所做的只是呼喊与细语,只有女仆安娜以温柔哺乳她。我前面也说了那个镜头致敬的是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也就是说安娜虽然身为仆人,但却最终走向了圣母的贞洁,这种欲扬先抑的人格塑造使角色变得立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用过相似的手法。

影片结尾,艾格尼丝死去,安娜被解雇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家族将代表救赎的圣母驱逐了,为故事整体蒙上了一层更加悲哀的意味(我记得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也通过黑人女仆迪尔西的革职情节,侧面表达康普森家族的没落)。最终安娜通过阅读艾格尼丝的日记,时间线又回到了过去,前面的室内沉闷场景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丽动人的室外自然景色,三姐妹与女仆在外愉悦地散步,美好或许也只能存在于过去的时间中了。这时,一切“呼喊与细语”都会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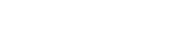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把心慢慢撕开的声音么?
1.几种阐释路径:宗教寓言、女权主义、疾病隐喻、精神分析。2.红色的封闭空间——三姐妹诞自同一子宫。3.四具女体构成两组对立:缺乏母爱的消瘦/宛若圣母的丰腴、袒胸色诱的纵欲/自残下体的禁欲。
观影感受: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呼喊与细语,概莫如此。
天空是油彩般模糊的蓝,呐喊彷徨是疼痛蔓延的红,冷漠恐惧是包裹身体的黑,承受一切的爱是大提琴谱写的白。我们该如何面对丧失和死亡,遗弃与残忍,欲望裙角下的罪过和谎言?谁看到我们的悲伤,也将拥有我们的爱。感激这生命中最遥远的拥抱,最绝望的孤独,最深刻的完美,
每次重看感受到的恐惧都在加深。伯格曼分而析之的冷静几近残忍,但终成“完美”的回溯才更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当意识到唯一无私的女仆安娜亦不过是与三姐妹无异的残片而已时。当然,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对人性的宽容。Cries turned into whispers and whispers into cries. Nobody hears, but we get by.
1.呼喊是恐惧还是虚伪的揭露,细语是亲昵亦是隐藏的伪善;2.呼喊是真心真性情的流露,细语是刻意是温馨的表达;3.隔阂太深太长久,即便红色的血停止流动亦是无法消除;4.温馨时刻的画面出现在死人的日记里,甚是庸人句读之...
红色转场,暖如子宫。特写的面孔
一部描述冷漠的电影却流露出对温情的渴望,这是它成为悲剧的原因。如针尖般纤细的焦虑在封闭的红色容器内密密繁殖,隔绝彼此,死亡也不能令其动摇
不说那么多,我只想说两点:1). 这片子基本上就是在写我 2).我要重新做人了
伯格曼的片子就是这样,有特别特别好的,也有特别特别装逼的,这部就是装逼典范,反正我是品不出这电影有啥营养。CC#101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纯粹通过内在情感而维系亲密关系,有血缘、契约、财产、性交,才有爱。
#重看#“我想留住这一刻,我想,不论会发生什么,这就是幸福,不会再有比这更美好的了”与《秋日奏鸣曲》在色彩和人物上都有类似之处;每个场景结束以半隐的特写淡出,“幕间”感;绝望的呼喊听来不寒而栗,这种刻骨的冷漠吞噬亲情和拥抱,让每个人都面目可憎,人人都在孤岛上或呼喊或细语。
美学登峰造极,内容令人崩溃
九十九分以痛苦否定希望,最后一分钟以希望否定痛苦。
1.一部倾泻着痛苦、绝望、疏离、圣洁等极端情感并拥有毁灭性力量的电影。2.触目的红:转场,墙纸,窗帘,地毯,白衣女性的四重奏。3.最擅长拍脸的伯格曼:以特写长镜袒露角色的灵魂,同质于[假面]。4.安娜裸身怀抱还魂的阿格尼斯,致敬圣母怜子像。5.晨雾庄园与短暂美好的结尾,钟表滴滴同[野草莓]。(9.5/10)
(长文→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116447/)扮演三姐妹的女人,伴随了伯格曼戏里戏外多少年!在这个冷得瘆人的空间里,大片大片的红反像血盆大口,或者血,追捕,又淹没了每个尚未窒息的喉咙。再浓艳,都是腥冷,姐妹间那种和美假象,一旦崩塌,彼此都迫不及待撕下面具张牙舞爪。一个阶级的冷,又更显另一阶级的亲善,且安娜的宗教意味甚浓。
伯格曼近乎自然主义地描写了晚期癌症病人在衰弱和剧痛中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结,为此他必须用唯美的画面和鲜艳的色彩来加以调和,才不至于让人彻底堕入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绝望。
那个时代的女人,根本不是人,无论她们看起来多么美丽,优雅,富有,本质上仍然是豢养在华丽动物园中的兽类,无法独立,无处可逃。但内心的渴望是关不住的,捂住嘴巴,就会从眼睛里跑出来,捂住眼睛,就会从紧紧握住的双拳中挣扎出来,直到最后整个人都变成一团烈火,烧伤每一个遇到的人,也烧死烧尽了自己。伯格曼一定见过很多这样的女人,他听见了她们的呼喊和细语,他想替她们说,没有一个生命应该这样活着。
三姐妹,室内剧,红色的意义。伯格曼式特写下的细节:痛苦,撕心裂肺,隔阂与祈祷,回忆。终极问题的回答。可惜年华逝水,旧日时光不可重来。
一部让人不敢标记的电影。真的可以看懂吗?多么私人化的东西。基本可以当恐怖片看。猩红之外就是一片雪白和漆黑。情节空洞到了基本不让人留下任何印象的地步,但特写里人脸上种种无法辨识的复杂情绪足以让人永世不忘。死人复活、表达无能和虚情假意,或生或死都是阴冷和抛弃。伯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