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母亲的镜子
《死者田园祭》是松竹新浪潮时期的重要导演寺山修司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实验戏剧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寺山修司先生在他的这部作品中用了不少实验戏剧的手法来进行创作,表现手法极其戏剧化,无论是人物脸上涂抹的白色颜料还是出现的怪异人物,都带着浓郁的日本传统能剧的色彩。

而在其情节以及叙事上来看,片中充斥着大量潜意识的元素、反战情节、私人记忆、恋母情结。用精神分析的手法,我们可以理清这部看似晦涩的电影其脉络。
影片中的主人翁即“我”,一个电影导演,妄图用电影去改变过去,从而与过去的自我相遇,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持续无法被治愈的人生。其中“我”的身份是多元的,他可以看做是当下时空自我的潜意识,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镜像。

雅克·拉康提出了“镜像阶段论”,人在6——18个个月大的时期通过母亲对镜子中身份的指认进而对自我产生了自恋式的认同,而这个误认将伴随其一生。克里斯蒂安·麦茨在《想象的能指》中提出,电影能使人重回婴儿时期,对银幕角色产生自恋式的认同。而《死者田园祭》中,我作为导演与观众,从自我经历中汲取灵感,又对再造的自我产生了认同。“导演”——“观众”的双重身份使其达成了一种双重误认,进一步模糊了虚构——记忆——现实三者之间的界限。而观众跟随着我的视角,也开始对自我产生迷失的错觉,造成一种双重镜像的迷宫幻觉。

联系导演寺山修司先生的自我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其自身身份与《死者田园祭》中主人翁“我”的惊人相似。父亲死于二战,家中只有母亲。父亲抚养他长大,有限制其成人。长期与母亲生活的他有着极其浓郁的恋母情结,而这种情节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电影中的“我”恋上了邻居家的少妇,她年长于“我”,与“我”的母亲有着相似之处,甚至可以看做母亲的镜像。而后来夺走我第一次的,也是一位母亲。母亲是“我”永恒的伴侣。而让我一种不能长大成人的也是母亲,她死死地护着家中唯一的表,不给我买手表,不让我拥有自己的时间。有了自己的时间,掌控自己的时间是大人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却是母亲不能接受的。不让我割包皮,割包皮是男孩的成人礼,而我却不能完成这个简短的血腥仪式。母亲是“我”成长路上的绊脚石,然而我却无法割舍。最后还是作为母亲镜像的另一位母亲,用她的肉体来给我进行了一场成人礼。

三位母亲,可以看做三堵镜墙,而第四堵墙向观众敞开。



我因此长大,想要烧毁一切,杀死母亲。身为导演的我似乎成功了,然而事情却没有结束。镜头一转,母亲仍在。我依然爱她,她仍旧爱我。构建的舞台坍塌了,“我”生活在现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东京,面向观众的墙一直敞开,而作为戏剧空间的墙也轰然倒塌。

我生活在现在,我永远无法改变过去,我不能够离开母亲,我永远爱她。母亲的镜子会伴随着我一生,这是幸福也是诅咒。
2 ) 《死者田园祭》 寻觅少年梦境和爱情
寺山修司少年梦境和困惑的集锦,优美的俳句点缀了整部电影,影片充满了奇思妙想使得视觉语言异常丰富。玄衣的老妇、穿着和服的女人生产、母亲掀起地板所看见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的样子,东方的玄学和死亡哲学在这部影片里被视觉的再现。人物都涂着浓烈的日式油彩让我们间离于存在之外,在想象的世界里和寺山修司的才华同行。和死者的对话反映的是寺山童年的寂寞和惶恐,这是孩提时代的印记,无法抹去。而导演在影片里一再出现的移门如同戏剧的幕帘让我们明白这一切只是心念里的幻象,一个寂寞少年向往的童年。而少年和邻家媳妇是私奔只是表明着导演心目里一个少年告别自己长大和成熟的开始。
在片子里导演表述了这样的观念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过去已是被记忆浓妆艳抹,再不确切。
所以,在真实的世界里,导演以黑白的画面来表达一种朴素的真实感。
在这个片段里我看见了寺山的先验,他认为时间机器是无法成立的(无独有偶,当下霍金自己推翻了这个理论)这种哲学的思辨让我们看见了诗人导演的智慧。当他再次回到20年前,他悲凉的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苍凉悲愤的歌唱在死亡的记忆里穿越。
影片的后半部其实是长大的我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思考,以旧我和新我的对话,提出了时间不可逆的命题,是诗人导演进行的一次思辨过程。
影片最后,景板倒下母子在东京街头的高台上吃饭的镜头是导演再一次希望注意所有到所有影像的虚幻性,以布莱西特式的间离让我们在沉醉里清醒世间万物的真相所在。
我。还有玩伴,在墓地捉迷藏,捂着眼睛的我看不见阳光,慢慢我从缝隙里看见有人,不是玩伴而是从墓里跳出的人。我害怕。
这是电影诡异的开始,你们将跟着我走回童年残破的记忆,在充满恐惧和灵异的世界里进行一次想象之旅。
童谣带着梵音在冬日葬母的路上,凄厉的风里行进着一群玄衣的老妇,巨大的佛像在山坡上凝视着死亡之地的硫磺火焰,
记忆是瞬间的,那个叫魂般的钟让我知道了时间,时间是钟摆上的刻毒还是它失控时的不停的达点,母亲让它牌位般搁在墙上是有道理的,时间的描述在于它周而复始的行走。
我是一个乖巧的男孩和母亲相依为命,以我的视点观察村子里发生的一切。
我目睹了一次生产,生产具有仪式性,它映照着母亲和我的关系,也在这样的观望里开始长大。
而父亲的幽魂老是回家,母亲通过地板下的洞能够看见另一个世界的幻影,而阻隔他们侵入的方式就是地板上写满的咒语。我特别的孤单,只能将心里话对着恐山上爷爷的幽魂说,而伴随我的还有一个充满诱惑的女性舞者。
流浪马戏团的在电影里更是让寺山的想象有了发挥的余地,电影的第一部分回忆以我和邻家女私奔结束,电影反映的是少年发现自己和了解自己的过程。
在电影试片室里,长大的我和人谈论记忆被修正的无奈,从而也反映出导演的观念,往事只是被涂上油彩的梦境和真实世界有着鸿沟。
影片以剪辑室大堆的胶片隐喻记忆的仓库,在那我和20年前的自己相遇了。导演有一次使用了移门将观众带回了绚烂的幻象世界。我们听到了悲凉的歌声。
20年前,和邻家女私奔的故事在继续,来邻家女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因为战争爆发,父亲音信全无,她和母亲失去了生活来源,母亲死后,她因为私生子的事为村子不容,直到她遇到了岚(原田芳雄)。导演通过我在恐山第一次感到了被欺骗的难过和岚给他抽烟表明了少年时代的结束,从此,他走向了城市,在生存和寻找里逐渐长大,直到20年后成为了导演,再次回忆年少的日子。
少年时代的马戏团是孩子幻象世界的入口和长大方式,这是主观的回忆和客观的相容,这是记忆里无法抹去的少年欢乐和美好时光。
影片的后半部分导演为我们创造了经典的一幕,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坐在草席上对弈,同时背景出现了各种属于人类的场景,婚礼和葬礼,这是生命的构成。导演让两个不同时空的人物对话,对时间的确定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识,生命只是被动的参与者,我们只能随着时间的进程按部就班成为未来的我,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钟在这个电影里成为重要的意象,成为生命的见证和标志。
影片最后导演在现在的我和过去母亲的见面,突然,景板倒下,我们看见两位演员坐在车水马龙的东京街头拍着这样的场景,导演以这样的手法告诉我们电影的虚幻性,而这样表现手法在日本电影里比较常见,这和东方人的哲学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死者田园祭》是诗人导演的个人记忆的视像化,是梦游年代和理性思考的结合产物,是导演人生观的产物。作为寺山修司的第二部长片他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他以漫游的手法让观众看见了一个少年的成长路程。
【附录:影片资料】
《死者田园祭(Pastoral Hide and Seek)》:日本1974,
编剧、导演、制片:寺山修司
摄影:铃木达夫
演员:八千草薫、新高恵子、高野浩幸、斎藤正治
片长:102分钟
个人评价:艺术性8,欣赏性7
2004年8月7日 星期六 18时48分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版权所有,请勿私自转载
联络方式:MSN:[email protected]
约稿邮箱: [email protected]
3 ) 一点笔记
片中字幕诗:
1 有买母亲的街吗?
2 针线盒里的针都生锈了
然而我和母亲之间的裂缝始终无法缝合
她终日在家擦洗那神坛 那是她唯一的嫁妆
直到它亮得能映出她的人造眼球
(后面出现一人背着木匣子叫卖:神坛,有人需要神坛吗?有人在意神坛吗?)
3 哭喊吧,小鸟,让我的妈妈好好睡个觉
在她坠落山崖之前
玩捉迷藏的小鬼们已经长大成人了
祭祀的村们在找谁呢?
4 我想把钟卖掉 但每一个人愿意买它
我只有带着它在荒原游荡
我和20年后的我
影片进行过半,“我”切断影片播放。我与其中的观影者交谈。他提出,你会去杀掉你的曾祖母吗?(杀掉曾祖母意味着没有现在的你)
我介入影片后半。我和少年的我有一段关于时间的谈话。最后,我要去杀死母亲。
最后,我并没有杀死母亲。我和母亲一起吃饭,我们身旁的墙壁倒地,我们和世界、我们和时空的屏障拆除,我和母亲坐在街边吃饭。至剧终。
意象的呼应
在诗中反复吟咏的母亲的红木梳,在隔壁夫人的回忆中再次提及。母亲去世后,她将红木梳埋在土里。她被迫卖身,红木梳浸染在血迹中。
影片开始红木梳在杯中,上面缠着一缕头发。后来我要离开母亲,在拉扯中,将母亲的头发拽下一缕在自己手中。
余下人物
疯女
疯女生下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疯女扔掉被村民诅咒的孩子,消失了。
她回来,从东京回来,举止浪荡。
在神坛面前,她强奸了我。
马戏团的吹气女
无论怎样都不会生气的穿着肥大塑胶衣的小丑
没有性的吹气女
每次欢爱都是一个男人给她打气
“她脱掉了塑胶衣
她一脱掉衣服,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的侏儒丈夫搭上别的吹气女,跑了
她说他会回来
一个人要掐死她
为什么你不生气
他们都以为她死了
她嘟囔着醒过来
马戏团没有死人和眼泪
只有欢笑和永生
手举红玫瑰的红衣裸女(赤裸地裹着一块红布)
在荒野
她妖艳地翩翩起舞
像是逃逸成功
像是灵媒的祭祀
女人躯体的自由
穿上才是罪恶
一朵死寂的拼命生长的花
独眼黑衣老妇人
絮絮叨叨 唾沫相迎
散布死符的巫婆
地狱的火焰随时撩到地上的人们
4 ) 青春祭
不是所有人的记忆都是完美的,你会找到我所丢失的,那就是所谓的成长,但是我不可能去找你丢失的东西,这已经过去很久了,太迟了。
======
电影《死者田园祭》的原作,是1965年发行的同名和歌集。这部和歌集由七个篇章组成:作者的家族史《恐山偈文》、恐山、犬神、摇篮曲、山姥、离家出走节、新·病草草纸、新·饿鬼草纸。每一章又被切分为更小的主题,除了短歌以外,还涵盖了戏歌[1]、草纸[2]等体裁。光看各章的标题,我们就能发现寺山修司反复刻画的那些意象。整部和歌集就是电影的灵感来源,其中13首和歌被片中人物朗诵。《恐山偈文》更被谱成了片中的插曲。不过,和歌集与电影中的和歌,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比如第5首,“我和……就快”改成了“我和我的……”;第9首中的“户山”改为了“下北”;第10首,“和鬼周旋直到老去”改为了“一直当鬼直到老去”;第11首和歌中的“亡母”变成了“亡父”。前四首,情节相当于是电影原创的。寺山经常在同一主题下,根据场合不同而对和歌做一些微妙的改动,再把它用到电影里;这一次,同样也是根据电影的内容,对旧作进行了加工吧。依照这些和歌在片中的出场顺序,我将在下面列出各自的小标题。但由于短歌的内容和片中朗诵时呈现的画面并不一致,姑且认为它们随机分散于全片比较好。另外,并不是全部的短歌,都按文字描述的那样影像化了。
1.大工町寺町米町佛町买卖老母亲之町存在吗雀儿哟(恐山·少年时代)
2.去买新佛坛时失踪了的弟弟和鸟(同上)
3.少女松散的头发编结出的是葬礼之花的花语么(恐山·恶灵及其他观察)
4.前往恐山埋葬亡母的红木梳路上冷风呼啸(?)
5.针箱里的针老化了我和母亲之间的裂缝也补不上(山姥·发狂诗集)
6.嫁妆仅此一佛坛她将其擦拭锃亮足以映出义眼(恐山·恶灵及其他观察)
7.被弃于浊流燃烧而至的赤色曼珠沙华是某人的祭品吧(犬神·寺山节传记)
8.为了得见光明将眼睑深深割裂剃刀之刃映出地平线(犬神·法医学)
9.哭泣吧鸢之子抛弃下北的念经老太婆以前的母亲长眠(山姥·旧话)
10.玩捉迷藏一直当鬼直到老去村祭在寻找着谁(摇篮曲·弃子海峡)
11.亡父灵牌的背面我的指纹在夜里寂寂消弭(犬神·寺山节传记)
12.烟蒂升起的烟指向北方若北方暮色深沉便不会思乡(摇篮曲·对暴力论书)
13.本来打算卖掉挂钟却突然横抱起它向荒野走去(恐山·少年时代)
第1首和歌,罗列的是青森的物品和记忆中的地名。我查了《日本行政区划图地名总览》(人文社),发现这些地名都真实存在,但其中几个有若干同名的。弘前寺有元寺町、元大工町,八户寺有大工町,黑石市有后大工町,五所川原市有寺町,大间町有寺町、佛町,风间浦村有寺町,鯵泽町有米町、佛町。青森很多地方都习惯以职业名来命名街道,除了上文提到的,还有桶屋町、锻冶町、纸漉町、铁炮町、渔师町等等。这些街道并不是寺山的居住地,因此我认为和歌中没有特指某些具体的地方。“米町、寺町、佛町”这些词的音韵和罗列方式,都经由作者安排。大工、寺庙、米、佛对应的街道固然存在,但是,可没有哪条街把老母亲当作商品,也就是说,没有哪里可以接收不被需要的母亲。这体现出了少年想要抛弃母亲的心情。结尾的“雀儿哟”跟前面的意象分明处在不同的世界。少年苦索而不得的答案,是否要向非人类寻求解答呢,影片中没有具体说明。
寺山的很多短歌里都出现了极度视觉化的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电影。比如第8首,就会让人想起路易斯·布努埃尔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1928年)的开头场景:月光倾洒在阳台上,女人的眼球被剃刀割裂。《死者田园祭》片中没有这样的画面,倒是展现了割裂之前的状态——主体是一位没有眼睛(本应是眼睑的部分被封住了)的邮递员。寺山说过“眼睑是最小的屏风”,电影最后一幕即是舞台屏风的倒塌,这也可以理解成电影的世界观遭到破坏,或者说“割裂屏风的行为”,不就正好是这首和歌的体现么。
短歌和电影画面最为对应的是第10首。影片一开始,第1、2首和歌以叠印字幕的形式出现在漆黑一片的荧幕上,人声朗读。随后慢慢淡入场景。墓地上,留着娃娃头的女孩子面朝观众,捂着眼睛问道“好了没”。我们这才明白,刚才的那一片漆黑,是在“捉迷藏”游戏中当鬼的小女孩,捂眼的手中的漆黑光景。之后,孩子们躲在墓碑的影子里,一边回答着“好了哟”,一边再次现身,然而,大家都成了大人模样。在捉迷藏过程中,捉的一方把眼睛捂住,遮蔽世界;藏的一方在某个隐蔽处躲起来,也与世界隔离。虽然只与世界隔离了一小段时间,但世界的面貌可能已经大不相同,少年(少女)的恐惧,跃然银幕。地点由短歌中的村里变成了墓地,是不是想要表现“永远地躲起来了”这一层死亡意味呢。至于短歌中“村祭在寻找着谁”一节,电影展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画面。
第10首和歌,寺山在其他作品中也多次应用。比如,寺山互换短歌中捉的一方和藏的一方的立场,写过这么一则小故事,“我躲在仓库的稻草堆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突然睁开眼,发觉外面已是冬天(也许有祭典)。一出门,看见伙伴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哄笑我:‘你不会还躲着吧’”。不管是电影还是这则小故事,主人公一方都保持着孩子模样,与短歌的内容有所矛盾。而与短歌的内容吻合的,是寺山收录在童话集《被红线缝合的物语》中的一则关于老人的故事,名叫《捉迷藏之塔》。如果在捉迷藏中当了鬼,那么在找到躲藏的孩子们之前,他们全都只想念着当鬼的自己,等待着自己,这样一来,自己就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所以故事中的老人,从不主动去寻找躲着的大家。就这样年岁渐长,老人如今已经玩了70年的捉迷藏,当了70年的鬼了。明明大家都和藏起来的时候一样,停留在孩提时代,只有鬼上了年纪,成了老人。“变老的从来都只有鬼”,故事就此结束。躲的一方,活在不断更新的时间里;只有捉的一方,被过去束缚,重复着空虚的时日,垂垂老矣。
小川太郎所著的《寺山修司~不为人知的青春》提道,少年时代的寺山,并不像自传中描述的那样是孩子头,实在要说的话,倒像是遭欺负的小孩。就算玩捉迷藏,他多半都被迫当鬼,说第10首和歌是在表现寺山少年时代的回忆,也是恰当的吧。其他的孩子都回家了,只有他被留在原地。尽管如此,当鬼的自己还是要不停地寻找,这样的光景不由得浮现出来。所谓捉迷藏,是寻找消失了的某人的游戏。这其中,说不定也反映了寺山渴望找到扔下自己,消失不见了的双亲——死于战争的父亲、外出打工的母亲——的心情。
寺山在《修正手相》一文中写过一首和歌,“为了让生命线默默改变,我抽出了一根钉子”,它与第13首的内容不无联系。据说,寺山从小就注意到,自己掌中的生命线很短。他想要做点什么让它变长,于是就试着往掌中扎入钉子,弄得鲜血淋漓。可是,等伤口愈合后,生命线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有一天,寺山决定去见见隔壁村那个能“修正手相”的老伯。他听说要拿500日元作谢礼,于是就把家里的挂钟拿去当铺换钱了。
我不认为这是寺山的真实经历。换言之,寺山在构思这些短歌的过程中,其实抱有“改写过去”的想法吧。电影《死者田园祭》里有这样的场景,少年的母亲抱着挂钟从恐山走下来的时候,恐山的山脊处,出现了十几个少年的幻影,他们也抱着一模一样的挂钟。这个场景里,挂钟的声音像幻听一样,不断在耳边鸣响。除掉“去卖钟”这一部分,这可以看作第13首和歌的影像化。
片中时不时会出现,一度残破之后用线缝合的母亲的照片。它虽然没有直接对应的和歌,但与第5首给人的印象有所重叠。想抛弃却无法完全抛弃,想憎恨却无法彻底憎恨,和歌和影像传达的,都是这种对母亲的别扭情感。寺山很喜欢用“缝合”这个词。和歌集《死者田园祭》里,除了有“为了缝合地平线/找到了姐姐藏在针箱里的细针”这样的和歌以外,“用红线缝合眼睑”之类的场景也多次出现。据考证,这源自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的第二支歌,“我可能还会用一根针缝合你的眼睑,将世界的风景从你眼中夺去,让你找不到自己的道路”。这与第8首歌(为了得见光明而割裂)的景象相反。寺山一面说着“想要看得更宽更广,不得不割开眼睑”,一面又说着“为了看见原本看不见的东西,要更黑暗才行!”。
片中的母亲,一有机会就仔仔细细地擦拭佛坛,简直把它当成已死的父亲的替代品了。这就是从第6首歌衍生出的情节吧。只是,母亲的眼睛并非义眼,也没有提到佛坛是嫁妆。
和歌集中有这些片段,“加入义肢县灰郡吧齿村”“木头变成了义肢村的义肢”“弟弟的义肢一下蹲就……”,但电影并没有用画面表现这些机械身体。关于佛坛,寺山也用过各种各样的刻画方式,比如安置在湖滨及道路正中央,肩负卖佛坛的使命而来,等等。
电影里,少年时代的我从熟睡的母亲身边溜走,离家出走了,这正是第9首和歌后半部分的情景。虽然片中没有像和歌前半部分描写的那样,映出鸢的样子,但偶尔会有乌鸦飞过,嘎嘎哀叫。这种印象上的重合,是不是想要借助乌鸦这一意象,展示恐山那地狱一般的氛围呢。我实际去拜访恐山时,也看到很多偷供品的乌鸦飞来飞去。将“户山”改成“下北”,也是想让人联想到恐山这一场所吧。
和歌集中没有与第4首一致的,但有两首很相似的歌,“一用亡母的红木梳梳理,山鸠的羽毛就不停地脱落”,“孤身来到即将出售的冬夜荒田,埋葬母亲的红木梳”。片中,邻居的妻子化鸟对少年说,“我半夜悄悄起身,把亡母的红木梳,埋在了已被卖掉的冬夜荒田里。”由此看来,影像化了的是这两首和歌中的后者。片中的插曲将两者融合,再次强调了恐山的印象。埋葬母亲的木梳,是在竭力反抗田地被转让这一遭遇,而电影又将这一情景进行无限放大。红木梳一到夜里就歌唱,红木梳在村中的田地恣意生长,成百地生长。
第11首,是以《寺山节传记》为题的10首和歌中的一首,为亡母而咏。“寺山节(setsu)”与寺山的母亲寺山初(hatsu)仅一音之差,电影中的母亲也叫“节”。现实中的寺山之母,和片中主角的母亲都没有死。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电影才把咏母的歌改成了咏父的呢。虽然片中没有出现父亲的模样,但母亲擦拭佛坛,少年让巫女以通灵之术召回父亲,跟父亲商量离家出走的事,这些情节都在反映少年对亡父的思念吧。
第7首会让人想到片中溺死婴儿的情节,第12首与被追杀的共产党人吸烟一幕有所联系,但它们都没有真正对应的场景。第2、3首也同样。
《死者田园祭》的这些短歌,不只是被电影引用了。寺山有时也会在原文的基础上做些改动,换上不同的小故事,把它们用在文章、演剧以及电台广播剧中。
第二节虚构化的故乡
《死者田园祭》上映的1974年,寺山修司还执导了实验电影《rora》、《蝶服记》、《给青少年的电影入门》,在电影之外的领域没什么大动作。演剧活动方面,1971~72年《邪宗门》上演,当时的《青森县的佝偻男》、《犬神》、《花札传奇》等等,可谓是集早期风俗主题作品之大成,这个时期的寺山修司,正朝着更具实验性的方向迈进。74年公演的只有一部《盲人书简》,它为第二年引起社会轰动的30小时市街剧[3]《knock》,作了铺垫。
1999年的夏天,我到访《死者田园祭》的舞台——青森恐山,留宿一晚。看过片中少年登恐山的场景以后,我一直以为恐山离人的居住地很近,而且四处蔓延着地狱景象,但现实中的恐山并非如此。从村里到恐山要坐40分钟的公交车,这个地方就像陆地上的孤岛,几乎没有易于行走的平坦道路。事实上,我由于试图体味少年的心情而徒步行走,最后竟然花了3个半小时才找到民家。途中蓊郁的森林不断延伸开来,满目岩石的荒野仅是恐山的周边一角。此外,四处沸腾的硫磺确实让人感到不似人间,但一到夏天,恐山的森林会披上新绿,湖水粼粼,这时的恐山非但不像地狱,反而美如极乐世界。电影中强调这里多么地可怕骇人,其实只是寺山自己心中的恐山罢了。不过,恐山的确和影片中一样风车林立,山上、路中间地藏菩萨的身旁,都有它们的身影。我是这样猜测的,恐山地处严寒的东北,花朵的花期很短,就算拿它们当供品也会很快枯萎,所以不如供奉一些颜色艳丽的风车。狂风一吹,花瓣就飘零了,但风车却乘风转动,平添美丽。除了恐山以外,电影还让风车扩张到了村庄和农田,安置无数个风车,浓墨重彩地突出了电影的幻想性。
在恐山吃晚饭时,同席的僧人给我介绍了一首和歌,“听到野鸡嚯咯嚯咯的叫声,是会想起父亲呢还是想起母亲呢”。僧人说,“今晚,先祖大人将要降临赛河原。请把这首和歌牢记于心。若是诚心祭祀,便能在梦里与逝者相会”。
寺山的作品里也会偶尔出现这首和歌,看来它真的源于青森。根据寺山的亲身亲历,它出自农村剧目《石童丸》中的一节。故事说的是,“石童丸为了寻访父亲而登上高野山,孰料无果而归,发现孤身一人的母亲已离世”。寺山把这个剧看了三回,最后都能随口哼唱剧中的高潮桥段了。和母亲相隔两地,独自过活的寺山,每看到高潮部分就禁不住流泪。无论对象是生者抑或死者,这种因相距太远而无法相见的孤寂之情,都是相同的吧。
身处恐山,确实能感受到一种生者与死者共存的气氛。我留宿的那一天,发现人们都是为了与死者相会,诚心为死者祈冥福才来这里朝圣的,似乎只有我抱着观光目的而来。寺山修司在故乡的时候,一定是无意识地来到恐山,却因此找到了自己的原点意象吧。
其实寺山并没有住在恐山附近(陆奥市)。成长于青森的寺山修寺,在自传《谁不思故乡》中写道,自己除了在美军基地所在地——三泽居住过以外,大部分的年月都寄宿在青森市开电影院的亲戚家,那里的实际情况,与电影中描绘的农村·风俗形象天差地别。远赴东京以后,寺山对故乡的情思日益见长。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寺山总喜欢说,“我觉得故乡存在于远方”,因为如果终其一生都待在出生地,根本就领悟不了故乡的意义。如果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无法省视自己的内心。去东京以后,寺山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故乡到底是怎样的地方,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便开始探讨“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先祖是什么呢”,继而描绘出了新的故乡之姿。
我认为,寺山之所以要以青森为舞台创作乡土风俗主题的作品,直接契机是,1962年他回乡以后攀登恐山的经历。那之后他一鼓作气写出了广播剧剧本《恐山》。寺山62年连载文章《离家出走的规劝》,某一章的标题里第一次出现了“死者田园祭”这个短语。同年,寺山为电视剧写的脚本中,标题也有“死者田园祭”。这部电视剧以青森为舞台,虽然有“青年与妻子打算坐火车私奔去东京”,“把母亲的红木梳埋进田里”,“作为嫁妆的佛坛”等与电影紧密相连的桥段,但内容上和电影没什么共通之处,可以算是乡土风俗主题作品群中一部尚不成熟的作品。《我的自传》提到,寺山从1963年开始写自己的成长史,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叙事诗《地狱篇》,其中的短歌部分被编成《死者田园祭》,1965年出版。
第三节《死者田园祭》中的故乡形象
电影《死者田园祭》,是寺山将心中的故乡形象——即加工过的记忆,随心所欲实体化的作品。那群身披黑色斗篷的老太婆,从不正面与人对峙,却在背地里说人坏话,她们象征的是地区性社会的阴湿与黑暗。少年目睹马戏团的耍蛇女和黑眼镜男在帐篷小屋全裸交媾,大叫一声“地狱啊”然后逃掉;寺山在《我少年时代的地狱》里描述过一次亲身经历,“父亲出征的那天晚上,和母亲缠绵在一起,被子里露出四只脚和红色衬衫,在亮如20瓦裸灯的月神照耀下,这些景象清清楚楚地印入我眼帘”,电影的桥段就是衍生自这次经历吧。吃花的巫女狂舞,男人在如血般鲜红的湖面弹奏低音提琴,恍若恶梦的光景,在恐山绵延。导演笔记里提道,“要把外部的景色、津轻海峡和恐山的景象带入‘家’里;要将佛坛、梳妆台之类的家具带往荒凉的土地、田园,以此来颠覆内外的概念”,故乡的家、家具、故乡的景色、幻想的经历与亲身经历,所有关于过去的回忆,都浑然一体了。因此,《少年俱乐部》中的“鞍马天狗”等虚构角色,也像现实中的人类一样出现在了电影里。跟故事情节没有关联的个性人物,不过是留存于记忆中的各式各样的“物品”——或者说“风景”之一,演员也只是和美术品、道具一样的存在。
影片的时间观也是扭曲的。少年时代的我和现在的我跨越20年光阴,自由来往;仅在两人下将棋的短暂时光里,草衣离开村庄奔赴东京,蜕变成时髦女郎归来。修学旅行中的少年一行,渡过三途川的桥,返回时已成了老人模样;少年在理发店理发,理完了,他也长大了。流淌了二十年的时间,溶为一体。
寺山的导演笔记里写道,“这是一个以青年自传的形式呈现的,虚构故事。我们要想从历史的咒符中获得解放,先决条件是,挣脱个体记忆的束缚。这部电影演绎的,是一位青年‘试着修正记忆’,从而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他说这“并不是无法改写的过去”,可以想见,寺山不断将自己的真实人生虚拟化,然后又在一个虚构的框架里描绘那样的自己。电影遵循的并非现实主义的现实原则,归根结底,它旨在展现天井栈敷[4]的戏剧世界。
令我惊讶的是,剧本里每一个角色都有个性化的名字,但电影中只有少年时代的“我”被唤作“小新”。这大概是因为,母亲经常喋喋不休地向儿子搭话,但相比之下,其他人物之间甚少沟通吧。少年对化鸟的感情只限于憧憬,对生产后被迫溺死孩儿的草衣并不十分关心。村民是乡土风俗共同体的一员,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个人特征。马戏团全员本来就是虚构出来的,自然就没有命名的意义了。影片最长的一对一交谈场面,发生在少年时代的“我”和成人的“我”之间。
不知是谁说过,“演剧里,登场人物在被人叫到名字之前,什么也不是”。寺山也在戏剧《蓝胡子城堡》和电影《上海异人娼馆》里体现过这个观点。有人问剧中立志当演员的少女“你是谁”,少女答道“目前,我谁也不是。但今后,我会成为某人”。《死者田园祭》也有这样的小插曲,“村公所的户籍主管,带着村民的户籍原件去向不明啦,结果有人搞不清自己是谁了”。名字,充其量不过是廉价的标记符号,寺山则把登场人物当作现象来塑造,例如,嚼舌根的黑衣老太婆、溺死无父婴儿的女人、邻居家美丽的新娘。
寺山的另一部电影《丢掉书本上街去》,则是相反的模式,片中明明叫了人名,但剧本里只写着“我”和“他”之类的,结尾甚至没有主创人员名单,倒是让所有主创和演员都露脸了,是想表达,只有脸才能代表那个人吧。
电影《再见箱舟》里的失忆男人,把自己的名字和日常生活的点滴都写在纸上,贴满房间。但写着写着,他就忘了自己的名字,忘了所写的物品有什么用途,完全想不起来了。他说,“就算再怎么写,我还是会边写边忘了文字的意义……总有一天,我会连字都认不得了吧”。但正是在连名字和用途都忘却了的时候,才会重新质问,这个东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弥漫于整部电影的,除了被影片世界观所束缚的意象以外,还有过于鲜明的母亲形象。母亲掀开榻榻米,底下展开的是恐山的荒凉景色,仿佛一切都是我在这个有母亲的家中,做的恶梦。寺山在文集《逆转世界史·英雄传》中,写到古罗马的暴君尼禄,“对尼禄来说,整个罗马帝国都是小阿格里皮娜[5]的胎内之物”;电影《死者田园祭》正好也给人这样的印象,那么也可以理解成,这其实是母亲手中的故事,或者发生在胎中的故事吧。贯穿始终的“赤(血)”的意象、水手服女学生被侵犯后脚边流的血、写着“居丧期间”的纸和母亲的木梳渗出的血、冬日荒田里埋葬的红木梳、溺死婴儿时顺流而下的雏坛[6]等等,很多场景都让人联想到女性的恶力。特别是,当“我”看到鲜红的宇曾利山湖[7]时,仿佛见到了被母亲的经血染成鲜红色的便器,那种厌恶感不言自明。
影片还有一点与胎内巡游这一猜想不谋而合,即,它含有结构复杂的剧中剧,随着剧情的推进,影片的结构一层层明晰。寺山一面虚构过去,一面时不时地插入其他视点来揭露这种虚构性。作为主角的少年,打算抛弃母亲,和邻居的妻子坐火车私奔。这是第一层结构。当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寺山突然告诉观众,至此为止的故事,其实是“我”这个真正的主角,所拍的描写自己少年时代的电影。然后“我”在心里呐喊,“田园的风景,才没有这么清新纯粹(中略)我的少年时代是我编织的谎言”,揭露了故事的虚构性。这是第二层。但是,“我”为了改写自己的过去,穿越到少年时代的世界,让虚构的层级变得暧昧不明。最终“我”还是没能杀死母亲,反而和母亲在少年时代的家中吃起饭来了。忽地,家的布景崩落,露出现实中的新宿街道。这一段作为第三层结构,再次揭露虚故事的构性;虽然不断映出现实的风景,但剧中角色熙熙攘攘地混入新宿街头(宛如寺山的市街剧),现实与虚构、过去与现在,彼此融合了。最后,所有景象消失于一片纯白,全片结束。
这与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中《胎儿之梦》一节异曲同工。虚构之外又是虚构的世界,以为自己早就诞生于世了,但其实一切都只是胎内的幻想罢了。这个困于虚构地狱、母亲地狱中的世界,在最后一幕被真正的现实街道侵蚀。
第四节无法替代的意象
寺山修司的电影,时常会出现一些完全照搬他脑内意象的场景,而且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这些意象。《死者田园祭》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要数草衣溺死自己的孩儿时,人偶雏坛顺流而下的场景了吧。这一情节的舞台提示如下。
“草衣怀抱婴儿,立于河畔。她虽然有所犹豫,但终于痛下决心,包裹好婴儿来到河畔,欲将其抛弃。婴儿边哭边随流水远去。草衣大叫着,捂住双眼。最后,她试图追赶婴儿,跌跌撞撞地踏入河中。河川上游,乘着红毯的华丽人偶,顺流而下。”
被杀死的婴儿是个生父不明的女孩,她脸上有痣,村民们认为这痣是犬神附体所致,因此强迫草衣杀死她。顺流而下的雏坛,是在为本该鲜活的人生饯别吧。但是,杀婴桥段并没有勾起纯粹的哀怜之情,反而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导演没有用真正的婴儿或可爱的人偶来扮演婴儿角色。虽然没有正面拍到婴儿的样子,但那实际是一具烧焦了的人偶。骇人的瘢痕肉块立马浮现脑中,而村民的说法也暗示了这一联想是正确的。即便如此,草衣仍然无比怜爱那肉块一般的婴儿,拼命保护她。寺山很爱畸形人这一意象,因为它能把日常场景变成祝祭的空间;寺山憎恨这个排挤畸形事物的封闭社会。婴儿的形象说不定就是为了体现这个观点而设。按照村里的习俗,婴儿只不过是有颗痣,就要被视为犬神附体而遭到排斥;片中马戏团之类的,处在价值观不同的世界,比婴儿严重得多的畸形人在那里照样大受欢迎。这一节中,兰妖子扮成丑陋的佝偻女(也是畸形人),唱一曲《惜春鸟》,更添悲情。
“姐姐吐血/妹妹吐火/谜样的黑暗/吐出瓶罐/瓶中纳有/蓝色的新月/指尖一碰/瓶身变细/在单人地狱徘徊/的你/盗走户籍副本/比血赤红的花/飘零/标记着/人类的恨意/失去影子的/天文学/是比黑更黑的/无家的孩子/带上银羊/与黄莺/我决心/誓死追寻”
歌词上下文没什么关联性,影片中也没有十分相符的画面。“在单人地狱徘徊”、“盗走户籍副本”、“无家的孩子”,这些语句像在描述草衣的遭遇,她生下生父不明的孩子,被村民疏远独自徘徊;整体来看,人们容易把它理解成一首咏唱女子的不幸,以及因求而不得而饱受孤独的歌。但据我了解,这首歌其实是以西条八十的诗《富野地狱》为原型的。寺山在《人生处方诗集》中介绍了这首诗,并如是解说道,“魔术、骗术、熊娘、飞头蛮、马戏、花札、刺青、海盗船、中将汤、命之母、口吃、赤面恐惧症、法医学、地狱、人贩子、人偶、绘本。啊啊,这就是我的幼年时代!”当寺山把这首诗改写成自己的作品时,我们与其思考其中诗意的关联性,不如把它当作幼时记忆片段的拼贴吧。
第五节有所关联的作品群
《死者田园祭》是一部体现了多重虚构的作品。如果要比较,我认为筒井康隆的科幻小说《早上的煤气珍珠》与之类似。这部小说同样构筑了多重的虚拟世界,第一重,讲述发生在“梦幻游击队”这款电脑游戏里的故事;第二重,讲述玩这个游戏的主角们的故事;而书写这部小说的作者,则是第三重世界的中心人物。这与《死者田园祭》的三层结构——伪造的少年时代、二十年后的我、新宿实景,不谋而合。小说的高潮在于,第一重世界中的游戏角色飞出画面,在第二重世界里打斗。随后,原本分处于三个世界的人物齐聚一堂举行派对,全书完。它突破了虚构的层级这一点,也和《死者田园祭》很像。(既然电影和文学是复制艺术[8],那么当它们在银幕上放映——或者以文字的形式印刷出来之时,不可避免的,所有内容都成了虚构的一部分。看来对于寺山来说,能够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壁垒的,仍然只有市街剧。)某种意义上来说,近年来的科幻作品特别喜欢以虚构的多重性——或称之为我们自以为的现实的多重性,为主题。比如,前几年的美国电影《黑客帝国》(1999年),主角就生活在电脑创造的与现实一模一样的虚拟世界里。人们从虚拟世界中觉醒,向现实世界的电脑宣战。又比如日本电影《阿瓦隆》(2000年),它的舞台是近未来,那时人们沉迷于一款假想现实(virtualreality)世界的战争游戏。主角踏进假想现实的深渊,发现等在那儿的是“现实”世界(指我们这些在银幕前看这部电影的人所处的世界),这一设定与《死者田园祭》共通。另外,寺山的作品中含有大量数字朋克[9]元素,比如摆出各种各样的机械,人类和物品受到无差别待遇;义眼、义肢等取代肉体器官(机器人);记忆被任意篡改(电脑空间)……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甚少感受到其中的科幻气息,大概是由于那令人惊恐万分的世界,足以隐匿其他特质了吧。比起近未来,寺山的舞台更倾向于前近代;比起有用性,他更习惯于着眼于机械的存在性与相关咒术,他可以说是停驻在充斥着中世科学与炼金术的世界。
很多评论人说《死者田园祭》和费里尼的《阿玛珂德》本质上是共通的,但我个人不这么认为。《死者田园祭》里的空气女拜托少年帮她充气,却说少年“完全不行呢”;《阿玛珂德》里烟酒店的大块头女老板逼着主角袒露胸膛,还欲求不满地追着他跑,这两个表现女巨人欲望的情节,不无相似。另外,狂女、对马戏团(杂耍场)的迷恋、幻想癖,这些关键词在两部电影中都有体现,但它们都是寺山在之前的作品中就反复刻画的元素。至于对年长女性的憧憬、乡村风光之类的,但凡想要描写少年时代,这些不都是一定会出现的么。不过费里尼的其他作品,倒是与寺山电影中实验性的尝试有不少共同点,例如,《朱丽叶与魔鬼》让幻想中的角色实体化,并坐上人力飞机逃跑;《船续前行》最后一幕映出了电影的拍摄现场,暴露了影片的虚构性,等等。
====================
译注:
[1]戏歌:打油诗。
[2]草纸:散文、随笔、绘图小说等,都可称为草纸。
[3]市街剧:寺山对市街剧的说明是,它并不仅仅是把城市及街道作为演剧舞台,而是让演剧完全遵循城市、街道的日常现实原则。
[4]天井栈敷:以寺山修司为首的先锋派演剧实验剧团。
[5]小阿格里皮娜:尼禄的母亲。
[6]雏坛:女儿节摆放人偶的架子。
[7]宇曾利山湖:恐山的火口原湖。
[8]复制艺术:可以理解成以复制已有事物为前提的艺术形式,如电影、近代文学、摄影等。
[9]数字朋克:Cyberpunk,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常表现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
=========
小村寒舍中,少年、母亲和狗生活在一起。隔壁有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少年惟一的乐趣就是进山听巫婆讲故事。少年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厌倦了,有了离开村子的想法。郁郁寡欢的新媳妇邀少年一起逃出村子,但在约定的时间,新媳妇没有出现……这是「我」少年时代自转影片的前半部分。放映间里,评论家和演职人员认为「我」总结得不错。影片继续放映。这时,放映间的门开了,20年前的我——少年走了进来,他说这部影片美化了过去……「我」和「少年」谈起了母亲和她的死……「少年」想去东京,但迷失了方向。「我」留在田园里等待,回来的「少年"却没有带来任何母亲的消息……
在青森县恐山山脚下的小村里,有一位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的少年。少年暗恋着嫁入邻家的女子。邻居是地主,婆婆统治家里的一切,女子的丈夫则是个软弱的中年男人。对少年来说,生活中最开心的事情是去见恐山的灵媒,听父亲给他的传言。一天,一个马戏团来到村里,少年从那里瞭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心生向往的少年准备出村,邻家的媳妇得知后要与少年同行。然而那媳妇却没有赴约,等待的少年独自在原野上入睡……画面突然转到试播室,几个制作人员和评论家们正在观看此片,突然,剧中的少年开门进来,指出电影过度美化了那段日子,于是开始讲述真正的过去……
本片是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参展片。诗人寺山修司根据自己的同名诗歌集撰写了剧本,并亲自导演了这部描绘自己少年时代的半自传电影,构建出一个风格独特的世界。影片的内容都是田间的日常琐事,围绕少年的生活展开,并无出奇之处。影片的画面则充满了美感。善于组织文字的诗人寺山在运用色彩景象等这些可视元素方面也展现出相当的才华。本片主题暧昧,剧情平淡,但画面具有诗意的美感,是一部风格鲜明的艺术片。本片入选1975年电影旬报评出的年度十佳影片榜。
5 ) 寺山修司
某老師竟然說寺山修司是垃圾,我真覺得當博士也不能說明你不是垃圾。
精妙絕倫的視覺語言。俳句詩歌散落其間。每部片子我都可以看很多遍。
寺山修司在日本并不是以導演,而是以詩人聞名。在日本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聲名大噪。
死時僅有47歲。
早負盛名的詩人,鬼才導演,去世后留下一批晦澀、綺麗的電影,戲劇和詩歌。一流的影畫結合的藝術家,他簡直天生就該擁有崇拜者。
視覺表達充滿智慧。詩歌的意向表達他全還原于影像。
他的片子大多被打上情色的烙印。
這哪里是情色?是浮世繪,是記憶的視化像。
6 ) 《死者田园祭》——你梦中的葬礼还在嚼着雏菊

据说很多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童年回忆,他们无法清晰的记得自己人生最早的那些年。于是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长河里,他们在记忆的洪流中呛水呼救,试图永远的游进另一条河,却悲哀的发现沾湿衣裳的,是同一片泪水。

第一次看寺山修司的电影:大量碎片化的潜意识充斥其中,被扭曲的记忆和模糊的感情所蒙蔽,过去和现在的“我”在棋局中对弈,时空交错的混乱带来大量的隐喻。似乎你不过是想在记忆中,拾起拥有过的娃娃,却控制不住瞥向当时熙熙攘攘的人群。

这是一片被美术的艺术侵袭的土壤,你无法预测下一秒的记忆是黑白还是彩色。每个人都在思潮里自言自语,疯狂的意象充斥着贫瘠的山村。在日本邦乐的烘托中,将荒诞付诸于最日常的吃喝中、将性爱具体为粗暴的占有欲、将剧情丢弃在没有结局的缝隙里,连恨意也蜷缩在了梦境中。

鲜血流淌在河里,河里漂流走纯洁女童的尸体;鲜血从处子的双腿间流下,即便堕落如地狱,也是因上帝遗忘的失误。嘈杂的马戏团带来了大世界的五彩缤纷,记忆被四分五裂的色彩热闹围绕。少年在这猝不及防的迎来了性萌动,只靠力气没有技巧的他完全不能给那副皮囊打进气,直到在神佛前被粗暴的强奸,终于决裂了生命的另一个走向。

在这部半自传电影中,“导演”虚构了童年的真相,却在出逃的岔路口戛然而止。被关闭的电影告诉观众,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导演在拍他的童年回忆,却因为回避了童年的残酷而无法继续。他从没能轻轻松松从母亲身边逃离,直至长大成人;他也从未真正爱过邻居的漂亮妻子,那不过是性意识复苏后的第一次梦遗。成年的“我”无法掌控过去的“我”,他始终孤身一人在回忆中冒险。

在“导演”的记忆中,村庄里的人快乐一如疯子,人们互相追逐、互相伤害。村子里的男人们不是在战争中死去,就是在战争中疯癫,而女人们祈祷神婆和神迹的庇佑,穿上丧服、捆绑欲望、不男不女。田园里的稻草堆成了一只只乳房的形状,美丽的田园,就在葬满死人的哀山脚下。日日充斥着太平与笑容,却刺骨一如寒冬。

片中出现了五个重要的女人:“我”的母亲、“我”幻想中的裸体舞女、“我”暗恋的邻居妻子、生下孩子却被迫杀婴的寡妇、以及终日团坐等待被充气的马戏团女人。她们共同组成了“我”的过去,以致于过了二十年,“我”依然没能他逃出她们的掌控。

母亲,在片中长了一副好似男人的面容,死人灰日日夜夜渲染着她的面容,与成年后的儿子面容惊人相似的她,或许在丈夫死后继承了他的面孔,转而放弃了自我的。她以血脉特有的、以柔制刚的态度缠住儿子,成为了个体独立的道路上最痛恨的包袱。而档人类有了道德感,这个包袱便永远放不下。在儿子试图出逃的那天夜晚,在儿子被窝外赤裸出一条大腿缠住儿子的场景,像极了乱伦的春宫图。

舞女,在埋葬了少年父亲的那座山上,一个身披破破烂烂红色纱巾的女人常在那跳舞,然而在她身上,你只能看到模仿土方巽的暗黑舞踏,女性的温软肌肤在裸露的山岩上摩擦跳跃,疾风像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试图撕碎最后的遮羞布。少年跟着她走向父亲的坟墓、又走向了神秘马戏团,走向成年要面对的一切苦楚。如果说她只是少年的一个梦,那么对于梦中的少年,她就是真实。

邻居妻子,全片唯一美好春节的象征。围绕在绿叶间、熟睡于藤椅上的她美丽不可方物。眼波如水、浅笑娇柔,这份美是少年出逃的力量,以致于过了二十年,成年变成“导演”的少年依然想要美化这个幻想。他与她私奔成功,走向已经被清晰标注好的未来。那只指引着未来的手,也被姜文用在了《太阳赵长生升起》中。然而导演不愿意面对的,是女人的美好背后的哀伤:她幼年时父母双亡、童年颠沛流离、少年靠卖淫卫生、成年后加入婆婆操控丈夫羸弱的家庭、中年与情人私奔后自尽。乱世之中生而为女人的悲哀已经刻在了她的骨髓中,那份恬淡的美背后竟是由惊心动魄支撑。

寡妇从怀孕之日起便成了全村的话题,人们怨恨她怀上了孽种,却又不问其究竟,为了保护婴儿不被杀死,寡妇不得不把它包裹起来放在河流中漂走,孩子却不幸淹死,寡妇再次成为众人口中“刽子手”的存在。她展现给了少年人性中最荒诞离奇的所在,直到用暴力教会少年性爱的欢乐与无助。

马戏团的女人穿着肥硕的皮囊,男人们以给她打气为荣。每当有人给她打气,就像在观看一场赤裸的性交,干瘪的身心逐渐被充满、湿润,这是男人们的伎俩,身为少年的“我”始终没有明白,为什么累的全身大汗,却依然不能令这个女人满意。

女人的痛苦伴随了“我”的成长,在诡异的童年真相里,处处无所不在的隔阂轰然倒塌,不再分割母与子、不再分割少年与初恋、个体与众生,生活随着无头的佛像一起回归平静。被绑架的时间由不得你放肆,既已无可挥霍,不如任其损坏。连画着脸谱恍若扮演舞台剧的人们也不再可怖,人人都是如此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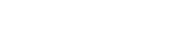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游走的虚幻与梦境,这一帧帧美的啊,我一不小心截了五十多张。求此片115已久,愣是没人传,好吧资源什么的得自给自足。【正片:t66517044a ,字幕:t69f80401c】
8/10。《再见箱舟》试图打破时钟的牢笼,本片又通过梦境与记忆的交错使生命超越时间这一维度。演员悉数白脸,万花筒装置艺术,撕裂的照片加剧了死味,浸渍般多色块的晕染镜头,圣母像的宗教隐喻,费里戏式马戏团,胖成皮球的女人,吞食的玫瑰花,标枪插流血的学生服稻草人,挑衅视觉是寺山的看家魔术。
1.我们都在被童年的回忆强奸着,而且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痛并快乐着。遗忘不了、挣脱不了;2.看完影片情不自禁泛着泪水,因为影片的内容,也因为不知道下一次要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精彩、这么厉害还让我心有触动的电影了!
流浪马戏团,隔壁美少妇。诡异少年梦,死在田园;墙上一座钟,地上一个洞。百年孤独史,再见箱舟。
寺山修司的最巔峰。記、憶、記憶三者粗暴地自腦海中被抽緒,卻又招展地在銀幕上先後麟次,是疊影也是軌跡;彷若在一疊印好的繪本上塗鴉、彷若在一場時光倒流的車賽上逆馳、彷若將一條新生兒的臍帶充作他未來自殺的吊繩,一切混亂與井然的共體,皆直通心智深處的渾沌真面。真奇觀也!
寺山修司你个迷人的大鬼才!
令人恐惧的童年 一定要整理和回顾才能走出来。而且与童年记忆的无助不同,现在有更强大的我可以陪着记忆中的我一起面对,我很强大,我可以搞定。以及对于母亲,厌恶还是爱着,不可能真的下手,到了“儿寒乎?”“欲食乎?”的阶段,也就只剩哽咽了。
寺山修司有三宝,乱伦做梦和钟表
妖艳而奇诡的视觉饕餮,记忆与梦境的光影诗章。墓地捉迷藏,恐山风车,白面与乌鸦,赤血红月,榻榻米下旋转荒青-山门-灯泡-颠覆内外。虹彩滤镜马戏,充气女颓坐呻吟,红衣女狂舞嚼花。缝合残裂相片,恋母与弑母,晚8~9时,捆绑与葬钟。私奔与铁轨路标,跨时空对弈,神殿童贞劫夺,现实侵入。(9.5/10)
此时心情犹如十八岁的李安首次观看伯格曼《处女泉》。
寺山的小剧场舞台剧画面有一种颠覆了学院审美的凄厉妖艳之美。若事情不似你想象:你萤火虫般的怒火并未烧掉苦闷的家;红衣女人淹死了被众人诅咒的私生女;相约私奔的邻家妇支走你与情人一同殉情;马戏团里洋娃娃般的天真女人最终被丈夫抛弃;你最终也没有能够摆脱掉被自己视为负担的母亲。臆想的童年啊
我以为自己能流出五彩的眼泪,却不知那只是寺山映画里空气的颜色。
原來新房紹之受寺山影響最深 堪稱二戰末期及戰後霓虹蛻變期民人社會心理寫照 此即日式傷痕文學電影的代表罷 極多典型徵符:無父的一代 破碎的抑或偏執的抑或作為異端的母親 殉情的共產主義異鄉男女 混合鄉國與外來者的夭折嬰兒 被迫現代化的女性 無法擺脫代表舊日歷史的母親 與受到現代文藝影響的兒子
7.5。看来许多导演的童年都伴随着马戏团与对成年女性的幻想。
《死者田园祭》。就像打开了记忆仓库的大门,四处堆放着影像化的碎片,现实和梦混杂难分,而由此"曾经"成为可塑造的,完成体验者的偏爱,但理智最终又不得不在时钟“嘀嗒、嘀嗒”的催促声里将一切拉回现实。寺山修司的影像常常令我感到像梦一样虚无缥缈,不但诡异,还充满森然的鬼气,令人生畏。
每一场光怪陆离都是支离破碎的别样狂欢。每一次生死离别都是如胶似漆的反向拉伸。每一次迟暮伤逝都是青春激荡的南辕北辙。每一次置之死地都是圆寂涅槃的晨钟暮鼓。
我们挣扎的七十年代,寺山修司已经掌握了足够超前的叙事手法。形式化到迷人的地步那其他的不足都可以忽略了吧,何况在预设的范围内你找不到任何问题
吓到了……寺山修司大白天净爱整些阴间操作,浓艳压抑的色调,堕落疯狂的情绪,神经质的思考,现实介入的荒诞,人物沦为导演表达想法的工具……这一时期日本拍了不少类似的实验电影,往往充满不明所指的意象又可尽人各方面解读,镜头语言无可挑剔,如果导演坚持有系列作品前后承接,一般就被称为“艺术”。。
美丽而哀怨的乡愁,精致如画,机巧如诗,是极具东方神秘主义特色的《阿玛柯德》,比较而言,寺山修司追忆童年的姿态在深情之外,明显还有迷茫、纠结甚至阴暗。
凌乱不失美感,象征性很强,颜色很绚丽,虚幻和梦境交替,看这个片子有一种东方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的感觉。同样那么虐心那么诡异和抽象的象征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