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一种奇怪的睡眠病在士兵之中蔓延开来,患病的士兵们噩梦缠身,纷纷被送往了一处临时诊所之中接受治疗。金吉拉(金吉拉·潘帕斯 Jenjira Pongpas 饰)是一名平凡的家庭主妇,亦是医院内的志愿护士,乱世之中,这座似乎与世隔绝的医院仿佛世外桃源般宁静且充满了启示。 阿肯(雅琳帕特拉·鲁安格拉姆 Jarinpattra Rueangram 饰)是一位灵媒师,她通过通灵的方式使家属们和那些患病的士兵们相见。莱特(班罗普·洛罗伊 Banlop Lomnoi 饰)亦是这些士兵之一,可是一直没有任何人来探望他,他的存在引起了金吉拉的注意。莱特有一本记满了奇怪图案和文字的笔记本,也许事件的答案就埋藏在其中。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小树的天空参孙的儿子夏洛克的孩子们电影版海鲜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2024侏罗纪入侵宕机警察第二季咫尺2002魔偶奇谭5邪神复苏全能侦探社第一季黄山来的姑娘属于我们的圣诞节解脱2024鬼娃恰吉 第三季无间道第三季龙宫女刺客之大明女监氪金男友紫外线牧羊人踮起脚尖去爱你摄影记者之死:阿根廷黑金政治秘笈追踪优步危机衰落与瓦解欢愉之书死于父手
长篇影评
1 ) 蔡明亮与阿彼察邦:论影像的亲缘性
2.扩展:(菲律宾)曼多萨的《情欲电影院》、(缅甸)约书亚•奥本海默的《沉默之像》;东南亚的热土,是空间-影像的天然加工场。
3.蔡明亮与阿彼察邦,《郊游》与《幻梦墓园》,变异空间与灵异空间;从《郊游》的三组并列空间类型:记忆、现实与幻觉,发展到《幻梦墓园》中三组空间的交互难辨:最后士兵从梦中醒来,前面借助通灵女孩与跛足女人发生的爱情片段,已经难辨虚实了。
4.《郊游》中,投放于公共空间的白炽灯,映照出现实空间的变异;《幻梦墓园》中,最为现实的空间也带上灵异之气:地下王国的公主走入镜头,没有任何的变异处理;跛足女人跟随通灵女孩探访幻梦墓园,在现实环境中想象完成。
5.蔡明亮的目光是现世的,未沾染上前世今生:是公共空间(商城、大型超市、面馆、厕所……)与私密空间(家室)的交互;阿彼察邦的镜头是超灵的,两类标志空间:医院(生死之界,沉睡是生与死的中间线)与森林(人与动物之界,注意《幻梦墓园》中那个野外大便的镜头,人生成为动物):是现实空间中发现记忆与幻觉,记忆与幻觉空间里保留现实。
6.影像具有亲缘性:因环境,因主题,因师承,因风格……;小津与侯孝贤,侯麦与洪尚秀、费里尼与大卫林奇、蔡明亮与阿彼察邦……
2 ) 关于“眠”的比较诗学研究以及阿彼察邦叙述语调分析
一、关于“眠”的比较诗学研究 《幻梦墓园》中,许多士兵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睡眠病,长睡不醒,他们被安置在一家医院。偶尔醒来,也会无征兆的突然睡去:吃饭时,正和旁边的友人聊天,突然便一头栽倒,沉沉睡去;和友人在夜市散步,聊天,又是突然睡去,只得拜托旁人抬回医院。 村上春树写过一篇名为《眠》的短篇小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与阿彼察邦的电影相反——则是失掉了睡眠,失眠了整整十七个昼夜。 与一般所谓的失眠症不同,不睡也不困,照常工作,晚上就喝白兰地,看《安娜·卡列尼娜》。 村上还写过一本中篇,《天黑以后》。也写了睡眠。浅井爱丽的沉睡,有大概两个月之久。只是多少不同于阿彼察邦的《幻梦墓园》。 浅井爱丽的“眠”是可控的,某一天,吃晚饭,她突然给家人说,我要去睡一段时间了。家人当时也没在意,然后她就这么一直睡过去了,一睡就是两个多月。也起来,饭菜的量也减少,也洗澡,但这些“只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理需要”。 而《幻梦墓园》中士兵的“眠”则是不可控的,他们会突然栽倒。 村上春树的“失眠”(《眠》)或者“眠”(《天黑以后》),相对来说,是非现实性的。 而阿彼察邦,除了非现实性以外,更多的,还带了些神秘主义。 二、阿彼察邦叙述语调分析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构思了15年,但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写第一句话。直到他某天读了卡夫卡,拍着大腿,“小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 “他娘的,我姥姥不也是这么讲故事的吗?” 那一句是《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就是这样的叙述语调,这也是马尔克斯迟迟不能下笔的原因,他说,“我还需要一种有说服力的语调,由于这种语调本身的魅力,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会变得真实。” 这个语调,不仅适用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也适用于村上的非现实,以及阿彼察邦的神秘主义。 适用于一切试图在其故事里添加荒诞非现实因素的幻想叙事者。 马尔克斯他姥姥讲故事的方式是什么? 用极平淡话语叙述极不可思议的离奇故事。理所当然,不以为奇。亦如童话,我们读《小红帽》,对动物会说话不会感到惊讶,那是故事世界的设定。同时其童话叙事的成功也在其叙述语调的“理所当然”。 ....... 而阿彼察邦的叙述语调也是如此:《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死去的妻子在餐桌显形,红眼黑毛变成鬼猿的儿子也来到眼前,大家一起坐下叙旧,让水让茶,闲话家常。 《幻梦墓园》中,两位女神祇显灵而来,变成凡人模样,金吉拉知道后略有些惊讶,但很快平复下来,让她们吃水果,一起聊着天。 以及还有可以通灵的女孩,让沉睡的莱特附身,带着金吉拉一起游走观赏“王国”。 最后,金吉拉和莱特醒来,两重空间。刚才的游走是幻想还是现实? 是梦耶,非梦耶,又恐非其真也。
3 ) 催眠的通感
首先它还是贴着鲜明的阿彼查邦标签,神鬼志怪,人与自然,生死无边界,超现实平常如现实,梦是一条丝,过去与现在穿梭来回。甚至场景和内容的自我反复与重温:灵媒说自己前世的故事(是从树上摔死的小男孩)和结尾插入的广场舞都和《恋爱症候群》有着遥相呼应的关系。
其次,它也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放大》、《百花深处》甚至张律的《胶片时代的爱情》,网球、胡同、吉他与墓园,真实与幻觉,存在与虚无,在特定环境下互为倒影和真相。
当然还不应该绕过蔡明亮。慢和老的美感,仰望月亮的意义,蔡明亮对此作出的解读,基本上也可套用于阿彼查邦的创作谈。这一理念作用于镜头,则体现为对时光的凝固。街面上路灯、医院里治疗仪器的颜色变化是不是有种以静制动的速度感?它就像红衣僧人近乎凝滞的行走,不知不觉,无声无息,落后时间也超越时间。因为你很难辨别光影是如何跳跃更替的,就像你看不清僧人到底在哪一刻迈过了身后。此外,电影院里的恐怖情色对应散场后的昏睡抬离,似乎也可牵扯到它与《不散》的渊源(蔡明亮的这部电影是阿彼查邦个人影史十佳的第一名)。结尾让人为之一振的音乐响起,像总结点题又像个性签名,也好比于蔡明亮的葛兰时刻。
那么,电影到底表达了什么?扼要地概括,它是三个人(士兵志愿者灵媒)在三种状态下(冥想梦境现实)穿梭三重时空(过去的宫殿后来的学校现在的医院)的相互融合和彼此感应:患有神秘睡眠症的士兵有着特异的感知功能(可以闻到糖的气味,能感受头顶灯光的温度,在梦中闻得到花香),看得到自己前世的灵媒可以和睡梦中的士兵进行交谈,有着奇怪腿疾的志愿者可以在日常里遭遇自己朝拜的神仙,在万物通灵的信仰之下,士兵借助灵媒得以附体,最后两人三角在梦里故地同游。具体到情感层面,它饱含对故乡的回忆和深情,也暗喻对国家的讥讽和抗议,它哀切于衰老带来的遗憾和悲伤,也寄希望于青春的指引和抚慰。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为了达成这种类似通感修辞的知觉体验,导演不仅将催眠幻术作用于影片本身,似乎还穿过银幕,直接作用到了观众身上。而效果得以促成,首先它是风格美学使然:不动如山的固定长镜,轻言慢语的人物状态,柔和的自然光,闹中取静的环境音,对戏剧性的转化消解而又若有所指,虚实之境的自由跳切而又如履平地……其次,因为内容本身就涉及嗜睡症,所以也不排除创作者的有意为之,翻滚的水车,旋转的风扇,上下循环的电梯,人员快速变换的湖边座椅,这些空镜刻意制造的单调、雷同和眩晕感,确实也像是一次带有针对性的心理暗示。所以或许可以这样结论,如果说志愿者和士兵最终相互入梦是得力于灵媒的指引,那在电影和观众之间,这次阿彼察邦就也充当了灵媒的角色,而且他还不分昼夜,直接白日造梦。
4 ) 对散步意识与催眠术的观察:内脏学
拥有散步意识的主体是自为存在着的,它既是意识的运动,也是一种显现为现象的固定的现实存在,这样的主体的身体也就是由它自己产生的关于自身的一种表示,纯然是主体借以显示其原始本性的客体。作为主体的诗意所观察的正是拥有散步意识的主体实现之表现的梦境形象,亦即主体的内意识本质所显象的现象与演绎的范畴,由于都是自为的、原初的存在,所有的内意识都可以以“人”的主体价值体系规定为作为有机体的器官与作为无机体的骨头,诗意在此所观察的正是器官与骨头在催眠术下的梦境形象。
眼球与政治
在所有的季节中,夏季是最年轻的季节,它把感性刺激放入内感官,控制我们的血液流动和器官功能。被丛林覆盖的家宅是青春的、富有少年气息的,里面仰卧着被政治影响着的器官,它们还可以排尿、充血、思考、幻想,但政治已取代他们的眼球。透过内感官意识,他们能冥冥感受到灯柱光色的变化,即使他们无法用眼球看见光色,但这些光色会透过政治影响他们的记忆,尤其是与他们散步过的街道、漫步过的树林相关的记忆:正是在夜间,在那被树荫包围着的青春家宅的夜间,灵魂交相传诵的食欲、历史记忆、感官经验在同样的光色转变印象中同化、无限化、秩序化,没有什么比寂静更能容得下这样的驯化了,我在寂静中进入这印象的空间,记忆中的声响——晚间摩托车的声响、电影院的声响、风吹树叶的声响、水车打在水面上的声响给印象重构了色彩,赋予它一个有声的躯体,这个躯体会在我们的耳边控制我们的灵魂、约束我们的言行,一种恐怖、无限、深邃的感觉在伪造的寂静中把我们紧紧抓住,这种感觉穿透了集会中的每一个人,让整个由政治主导的集会被黑暗的巨大静谧所迷惑,使集会也成为一个内感官的存在、成为一个具有印象色彩的躯体,它在夏日的夜晚之中,由夏夜的微风、嫩绿的树叶、清凉的湖水构成,它们如人体器官一样有节奏地工作、发出声音,进而催眠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相信自己被一所古老而坚固的家宅保护着,当我们觉得闷热,它让我们相信这是因为家宅外太寒冷,而家宅正与寒冷英勇地斗争着,正如我们的皮肤为了保护我们的内脏而与外在的寒风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变化着的灯柱已成为人性的存在,我们的灵魂便躲避其中,向它倾诉我们早已忘却的记忆,印象中的色彩如母亲的爱直达我们的心房。这是多么伟大的催眠啊!政治糊弄了我们的眼球,诱导我们把光色的印象当成了我们灵魂的母亲。
肠胃与语言
风雨过后,从树叶丛中落下的雨水嘀嗒就这样在闪烁,它使光线和平静如镜的水面发颤。看到这水滴,就会听到颤抖声。当眼球重新回到我们的外感官后,我们与家宅之外世界的联系逐渐明显、牢固,我们的血液流动也逐渐加快,肠胃开始蠕动、开始思念食物,当食物透过眼球刺激内感官时,唾液已潺潺流动,肠液也暗暗涌动。当所有的唾液、胃液、肠液都得到满足后,嘴唇和牙齿会产生快活的景观,灵魂会喜形于色,通过语言表达出它们肠胃的快感,此时目光不再在指挥,词源不再在思考,只在痛苦中在快活中,在喧闹中在平静中,在嬉闹中在抱怨中,我们的行为如同在肠胃中蠕动的食团一样随意,听到唾液、胃液、肠液的流动声,如此动人、如此简洁、如此凉爽,好像随水车一起涌动的湖水,发出湖水的特别的叹息声,那种与我们的灵魂、身体、思想同步的叹息声,带着一丝忧伤、一丝淡淡的、展示的、流淌的、不可名状的忧伤,那是源于奴隶道德的一种同情,让灵魂惋惜在梦境中被规训的内感官并思念那规训自己意志的光色印象。肠胃可以代谢食物残渣,但肠胃无法过滤灵魂对政治的同情;土地可以代谢人的遗骸,但土地无法过滤试图主导一切的权力意志。如果说有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肯定是肠胃对食物的同情和灵魂企图主宰食物的权力意志!爱乐至极,话语便可颠三倒四,如溪流嬉笑着、细水流淌这,不会有任何干涩,似钟声一般如期而至,带着夏夜般的具有青春活力的青绿色声音——在我们的灵魂聆听大雨声、阵风声时也会听到的声音,语言从未如此这般湿润过,浸透了空气与身体,生出了白云与草履虫,在孕育的意志中灵魂感受到了生的纯粹的喜悦,那是肠胃第一次消化母乳的喜悦,口腔会通过发出“妈妈”的声响传达肠胃的喜悦,这是身体对灵魂的唯一一次凝视,它不在可以思考的记忆中,而是在语言的表达中。
骨头与音乐
灵魂在内感官的家宅中是无限的,骨头替灵魂规定了家宅之外的界限,同时,骨头和内脏相互通过对方规定自身的形象、形态:内脏通过骨架来规定内感官的家宅的结构;骨头通过内脏凝视主体的灵魂,骨头与内脏组成了相反力量的辩证法,它具有是非辩证法的判然两别的清晰性决定了空间意义上的内在与外在和时间意义上的短暂与永恒,可以用最简单的几何学解构梦境——通过四肢的运动来画出梦里的宫殿和内脏的喜悦,如音乐一般将兽性快感与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反映灵魂的丰盈和生命的欲望。骨头在凝视灵魂的丰盈和生命的欲望后随着音乐舞蹈,舞蹈带来人格的富有、内心的丰盈、洋溢和发泄、本能的健康和对自身的肯定,这些本该都是属于我们身体的,因为它们都来自我们所熟悉的经验的世界,在催眠中,灵魂脱离了骨头去追寻色彩和欲望,又是骨头帮助灵魂找回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音乐把所有的身体聚集到一起,带着亲切的、乐施的、善意的信念去舞蹈,使自身生命充实,为了享乐而生活,却讽刺你争我夺互相倾轧,这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也是更自然的社会,因为自然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只要求保持骨架的完整,这样人们才能回到现实、回到这个以音乐为本质的世界。这里的音乐不似艺术般狂热,也不似美学般虚幻,而是如自然般真实。艺术会腐烂,美学会消散,唯有音乐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5 ) 短评写不下
阿彼察邦的电影总能带人回到十几年前,但是这部才六年前,怪不得又有跨国网恋又有智能手机。霓虹灯、气功治疗、鬼神、大通铺的医院、残疾这些都将人带回童年,而且是没有怎么见过表现的童年。开头我以为自己看的是热带疾病,过了半个小时才发现是这部,走神时候想鬼片果然还是需要一点信仰在里面,小时候的港台鬼片比较吓人就是有信的因素在里面,神和鬼出现才会自然而不搞笑,恐惧和环境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土壤没了编的东西自己不信也说服不了他人。
到四十多分钟神庙里面塑像上的神仙就那样穿着寻常地坐了下来讲述宫殿吸人精气的时候有被惊艳到,无论是宫殿而非美女这非常态的“妖”还是吸人精气这个在汉文化圈很好懂的概念。霓虹灯闪烁时候发现像蔡明亮是真的,台湾元素也多。
走在公园/宫殿上时的两个时空依然非常精彩,想到《十分钟年华老去》里面陈凯歌的《百花深处》疯子看到的是宫殿古董,其他人看到的是废墟。阿彼察邦直接不用其他手段表现宫殿,只在交谈中存在另一个空间。而且空间和现实空间又并存,有着新种的树,也有废墟的残存雕像。大妈当主角也非常厉害,《恋爱症候群》短暂出现过,这里成为主角,为爱痛苦又十分善良的言情剧女主,其实也可以是长相普通的残疾大妈,带点迷信所以轻易接受通灵,在老一辈与新一辈之间。
6 ) 白日做梦Cemetery of Kings
超现实电影,就是做一个梦。
这一点在这部电影里得到很不错的诠释
架空的时空和架空的历史。 不看到一段时间仍会一头雾水。但奇怪的是,一头雾水却也乐于其中。
时不时出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哲思话语和颇有深意值得解读的人物对白。
不论是所谓殿堂里的公主,还是通灵者,金吉拉就像是一个梦的引导者。她无比清醒,而我们在做梦。
偏冷色的光线处理和几近凝固的叙事时间
霓虹灯管背后满满的反科学和诗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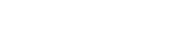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旋转不停的吊扇和桨叶,上上下下的电梯,颜色渐变的绚烂灯柱,来回换位坐下的休憩者,神与人日常式的交流,梦与现实交织畅游回溯历史,皆为一次用幻梦表达的清醒启示录。看完只想随之安然入睡,做一个闲适的抚慰伤痛的梦,然后记得睁大眼睛醒来。【2016十佳No.2】【2010s十佳No.6】
6/10。幻象的视听语言充满了黑夜,尤其一组画廊装置艺术般的连续镜头里,森林绿和红蓝光的病床旁灯管映照在商场自动扶梯的叠化影像,城市陷入朦胧沉重的肃静之中。大约97分钟时爬过云朵的草覆虫,起重机、广场舞、佛教雕塑、恐怖色情影院等重复的视觉母题,遗憾过多家常对话的白天部分破坏了整体意境。
还是邦哥风。但有一个地方不太理解:既然你都很诗意的把拉屎过程拍出来了,为什么不把擦屁股也拍下来呢?难道擦屁股就比不上拉屎美观和诗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更加成熟和诗意的阿彼察邦,剧本非常迷人,浅睡眠中的知觉拿捏。极简固定镜头下的丰富幻境,贫瘠乏味视觉中竟然会带来壮阔的想象。热带总是盛满可能性。当然,也很好睡。
探索时间与空间在电影中另一种打开方式应当的,但是电影不是这么枯燥的。导演的风格受蔡明亮影响很大,但是不得精髓,困意十足。
已逝的地下王国公主就这样走出来介绍自己,和生者交流,沉睡的士兵在黄昏的梦境里醒来,和生者一起逛夜市。挖土机不断地出现,环境在巨变,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维系(医院)或许也将随之被斩断。阿彼察邦对故土、人和神的热爱与敬重,都在这部电影里了。
阿彼察邦最近的一部长片,自我重复,了无新意。
论导演懂“建筑”的重要性。
胸外科下午3点全病房集体雾化的场景一下带我回到了这部电影
邦哥,我眼瞪得再大也真心伺候不了你。。。
導演很懂得創造電影的空間幻境,於是現實與夢境、現代與古老、今生與前世、當下與記憶、文明與自然、視覺與寓言全都疊合在一起,閑適的節奏卻深藏厚重的情感,或許比起前作是淺白了一點,但之前看過兩部導演舊作都睡著,這部新作就算是緣份到了。
阿彼察邦的片子里,人鬼神总能和谐共处,新作不玩视听实验,将神秘主义内核与写实主义形式(环境音,自然光,中远景固定长镜)融合。嗜睡,双腿不等长,国王鬼魂与士兵,挖掘机等元素有政治隐喻色彩。电扇-医院的流动变色灯管-河边-长椅-电扶梯一段大赞,渐变光彩仿若空间遥感。空中草履虫,桨叶,恐龙。(8.5/10)
各种催眠暗示用的很棒,这些催眠暗示也用来区分梦境和现实,同时构建出多重时间的概念,就像在记忆中行走,最后借时间和士兵的身体隐喻政治环境,是一部需要调动想象力,跟随潜意识和知觉观看的电影。导演这次没有在结构上玩实验,反而在情绪和心理上走的更深了,片子看上去很简单,其实非常复杂。
義無反顧五星。片首掘土,越翻越蒼涼。嗜睡士兵宛如影射一戰後的睡人腦炎潮,真實的霓虹治病科技成為科幻再成為魔幻。誓不兩立的又再雲淡風輕地二合為一。洗盡鉛華,一個行空之鏡都不給予。歷史與夢境與靈魂與華麗只在敘述裡。踢球踢到大沙坑,是的,我們甚麼都可以適應。生涯原是夢,醒也醒不來。
这是什么鬼?无聊到极致了…
看完,可以睡个好觉,做个好梦。热带嗜睡症,病房不停变色的灯管像未熄灭的神经元;漫长的晴朗天气,知了聒噪白云奔跑,水车旋转,屙野屎的人藏在丛林中一片寂寞;短暂的黄昏,士兵醒来在夜市,通灵的女人,前世今生,都是别人的事,郁热中不知所以。依然是熟悉的演员,以及导演标志性的广场舞镜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4星,可能是情节的奇异感和邦哥不正常的大脑非常匹配。居然看出来一点点情节,这不科学。当然,有情节也一样是看不懂。里面的装置倒是挺美的。
我看再過幾年,阿比查邦、蔡明亮跟趙德胤的彼此差別只會剩演員口音.....
#BIFF# 更成熟更讲究也更有诗意的阿彼察邦。怪异的霓虹灯配医院里长眠的士兵(精气被地下古老的王汲取)、结尾工地高低不平的土堆上的足球赛、通灵者和公园那段都像装置艺术般,展现一种被建构的场景(寓言/谜面)。
独特的影像世界。对于一个受尽欧美电影语言教育的人,总是在快要睡着的一刻被他的娓娓道来的叙事方法、神妙的用光与布景弄醒。喜欢沉睡的士兵身边变幻的治疗灯,后来整个世界都开始变幻色彩。梦境与现实不可分割,通灵女带领志愿者看失落王国,或是梦中世界,亲吻怪异的伤残大腿,人与神灵吃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