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二十四城记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曾经的繁华荣耀,随着时光流转与时代变迁渐渐褪去耀眼的光环,留下的则是无尽的落寞与慨叹。420厂(成华集团),一座从东北迁至四川的飞机军工厂,在特殊的年代里它曾是无数人羡慕与自豪的所在,然而和平的气息和体制改革却将它的光鲜逐渐销蚀。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它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而今旧厂址易作他主,一片现代化的楼宇将拔地而起。 大丽(吕丽萍 饰)、小花(陈冲 饰)、娜娜(赵涛)以及众多新老员工见证了厂区几十年的变迁。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万千唏嘘连同那旧日回忆随风飘散……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美人三嫁最佳导演猎杀圣战约翰舞会惊魂3:血夜回魂爱情同课程2妙手情天机器之血以恶之名联邦调查局第七季一个人的收藏 一個人的收藏九个半星期亲爱的孩子第一季都市热战追爱计中计刀马旦来自远方2021达科塔黑白游龙2023黑手遮天第一季邻座的怪同学(国语版)噬谎者-鞍马兰子篇/梶隆臣篇优越的一天野生狼性科南我们的纪念册蓝与黑
曾经的繁华荣耀,随着时光流转与时代变迁渐渐褪去耀眼的光环,留下的则是无尽的落寞与慨叹。420厂(成华集团),一座从东北迁至四川的飞机军工厂,在特殊的年代里它曾是无数人羡慕与自豪的所在,然而和平的气息和体制改革却将它的光鲜逐渐销蚀。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它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而今旧厂址易作他主,一片现代化的楼宇将拔地而起。 大丽(吕丽萍 饰)、小花(陈冲 饰)、娜娜(赵涛)以及众多新老员工见证了厂区几十年的变迁。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万千唏嘘连同那旧日回忆随风飘散……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美人三嫁最佳导演猎杀圣战约翰舞会惊魂3:血夜回魂爱情同课程2妙手情天机器之血以恶之名联邦调查局第七季一个人的收藏 一個人的收藏九个半星期亲爱的孩子第一季都市热战追爱计中计刀马旦来自远方2021达科塔黑白游龙2023黑手遮天第一季邻座的怪同学(国语版)噬谎者-鞍马兰子篇/梶隆臣篇优越的一天野生狼性科南我们的纪念册蓝与黑
长篇影评
1 ) 二十四城记:一个厂,一座城,一个国
厂是420厂,城不是成都,国却是当下的中国。
一、言说
贾樟柯无疑是十足自恋的,这里的自恋没有任何贬义,而是说他对自己的电影方式和自己的生命情有独钟。《二十四城记》在贾樟柯的作品序列中处在一处转折点,贾樟柯用这部影片对此前的作品做了一次有趣的总结。原谅我只能用“有趣”这个词,当然也可以说是奇妙的,因为这部片子在我的视野里,是中国电影序列里仅见的“仿纪录片”(Mock Documentary指用纪录片手法和表象拍摄的故事片。当然“纪录片”这个词本身也是裂隙纵横,至少包含了三种以上的不同影片类型,此处从略)。而这次影片又像一次长长的注目礼,对贾樟柯自己的电影作品,更是对中国当代史的后半段——于是我知道贾樟柯无论是从表达欲到叙事野心,都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部影片显然是过分表达的,因为“表达”或者“言说”甚至成了直接的表象和影片的主部。此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在大银幕上看纪录片(无论是哪种的纪录片)的经验——最多是在教室看过投影。这一次我的震惊体验大概与超级写实主义的油画类似,影院的大银幕上访谈和“访谈”的单调构图对我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而贾樟柯的策略,或者说影片结构,则是“真假参半”,用访谈和记录引入规定情境,然后再用一样的手法——被放大的“言说”——来进行叙事。试想倘若不是吕丽萍陈冲赵涛陈建斌,那么她(他)们的“扮演”行为是不是仍然能够被指认?或者,那些“受访者”同样也是在“扮演”?这里涉及到摄影机本身的权力问题,也就是说在摄影机下展示出来的是否还是“真实”,那么贾樟柯的回应则是两种——第一,有且只有言说,而言说的内容只好请观众“脑补”(脑内补完);第二,用职业演员的扮演在某种程度上提示这一“言说”的实质。换言之,我们并无必要去追究那些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当然可能有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在一本或者可能存在的《成发集团发展史》中有记载;或者也可能有一个酷似陈冲的上海姑娘——但是这些不是重要问题,重要问题在于这一切的呈现方式。
因为“言说”这一表象的存在,以及前30分钟的访谈和后75分钟的“访谈”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互文关系,有必要强调的是,“访谈”中的“故事”可能是特定场景下的故事,也可能是对生活的某种提炼。实际上除了第一个访谈,此后的访谈都具备充分而完整的故事性,它们就是故事本身,由此也再次对故事进行了自指——贾樟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如果不用这种手法,这部片子要么是一个N段式电影,要么是一个依那里图式的多线交织的后现代故事片。
于是从这个表象入手,对《二十四城记》的解读就会完全改变,因为首先重要的不是影片内容而是影片的形式——对纯形式的解读完全可以导向某种意识形态批判。当然可以把这种手法理解为缺少投资和缺乏能力——试想以这部高清数字电影的成本如何能cover一个跨越40年的史诗级别的故事?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贾樟柯的这种手法是有意为之——至少他不隐藏导演和摄影机,并且曝露了故事的讲述机制。
二、叙事
或许刚才的分析会导致对这部电影“形式大于内容”的判断。而就影片试图表达的内容而言,无疑是大大溢出了影片的范围。影片呈现的是一段历史,那么这部影片自然进入“当代史叙述”的序列中。420厂的历史,与中国当代史基本是等价的——从“以小见大”的角度来说。虽然当代史的禁区依然是禁区,比如文革(第一段访谈里的武斗),比如八九(好像与本片没有关系),但至少贾樟柯还讲到了不可绕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去年对新时期的回顾之中绝少提到的话题。当然大书特书的则是93年资本主义化进程开始之后的“分享艰难”,呈现方式则是讲述之中对“昔日荣光”的怀念和受访者无一例外的眼泪。贾樟柯最娴熟的技巧——用流行歌曲来标定时代——又一次成了他在影片中的签名,也是他一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结构当代史的方式。
受访人物的出场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建厂之初一直到现今的“80后”。一共8个受访者,其中4个演员,3个“真人”,剩下一个赵刚——大概能各算一半吧。这也是颇具形式感的安排。贾樟柯并无意通过他们的讲述构筑一个整体的叙事,但这些生命片段的交织却产生了某种蒙太奇层面上的意义。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讲述出来不过也是如此几句。在这些讲述之中,我们得知了420厂的变迁——它着实是一处“飞地”,如《世界》里的世界公园一般,超大规模的移民,一个工厂甚至成了一个小型规模的城市——有学校、电影院、游泳池,大量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人——大型国有企业的普遍处境。似乎用“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来下按语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部影片里的“工人阶级”多久没有在影片中出现了?曾经的“工人阶级专政”似乎也不再作为一个常见的提法了。而最后工厂变成楼盘,似乎也是某种当下资本取得胜利的隐喻。于是成都终于把曾经的飞地吞入肚中,荣光无限的工人阶级也光环不再,终于还是在社会巨变面前成了各谋生路的市民。
就“当代史书写”而言还可做出一篇大文章,但无论如何,贾樟柯这次展示出来的却是从《站台》一以贯之的视野,而《三峡好人》之中的潜台词——郭斌曾就职的工厂,以及作为“福建女老板”的翟永明开发的地产——在这里被详细的呈现。贾樟柯作为“70年代生人”的自觉使得他对80年代的叙述格外地精彩,附带地也造成了某种断裂和含糊,尤其表现在某种“更久远”的历史的状态下。
三、观看
贾樟柯的风格,或者说是“作者要素”,在影片中依然熟悉,比如逆光的窗户——得自侯孝贤的一种构图方式,还有很多,比如举着吊瓶的吕丽萍等等。当然非常明确的一个前文本是《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同样在处理“拆迁”这个命题,于是很多镜头都很相似,贾樟柯式或者余力为式的小横移,但由于高清本身的问题使得运动镜头不太流畅,还有最后一个俯瞰成都的镜头,明明就是《三峡好人》的情绪的延伸。于是《二十四城记》同样具有了某种史料价值,我曾在对《三峡好人》的评论中说“《三峡好人》真正所讲的故事是后工业时代中国的一个城市如何将要被废弃,如何正在一点一点消失,从而构建的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寓言。”而《二十四城记》要讲述的则是更深刻和更直接的层面上的问题——不是因为要建水电站,而是因为资本的介入;不是一个城市的消失,而是某个与红色历史相关的“飞地”的最终消失——这是否也是对红色历史的某种评判我不得而知。
然而还可引起注意的是访谈人物的选取,女人——四个女人,尤其后三个,承担了不同程度上的悲剧。如果不是毛的军工企业“靠山方针”,那么侯丽君的母亲与外婆是否不会分离十几年,是不是那么多东北人不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四川,是不是大丽丢失的孩子能够被找到,是不是顾敏华不会陷在成都和上海的夹缝之中而孑然一身?这些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但是有趣之处在于,女人们的讲述和男人们的讲述是完全不同的。除开第一位受访者何老先生,陈建斌扮演的副厂长和作为主持人的赵刚显然都是成功人士,或许是我的误读,或许也是《渴望》以来的中国情节剧苦情戏的传统使然。当然最精彩的段落是陈冲的20分钟——首先视觉上呈现为人物和人物旁边的镜像,而顾敏华和小花本身也是一组镜像,在加上陈冲这个集两个角色为一身的演员,实在是颇为精致的结构。当然导演安排陈冲观看电视中《小花》的段落,于是这就呈现出一组“历史的镜像”,影片的结构意义从而也被揭示出来:那正是处在当下的人们对历史深处自己的回望,以及注目礼——是行礼,更是送别。
放在“第六代导演”的序列里,作为核心表征的“自视”依然在这部影片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过《二十四城记》更像面对心理医生的一次访谈,结论,大概是最终的疗愈吧。
至于贾樟柯刻意不让身为易太太的陈冲打麻将,而让赵涛扮作王佳芝去香港跑单帮,只能看做是他的恶趣味……
四、贾樟柯
最后要说的则是有关“电影的事实”。贾樟柯作为新科金狮导演和法国电影界的至爱,本片入围戛纳理所应当,但是获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评委大概完全不知道这部电影在说什么。有趣的地方是本片在国内的某种程度上的悖反——评论以批居多,票房却是意外的好,上映三天过百万,虽不及某片和某片的一个零头,但终归是小贾老师的个人票房最佳了。
至于原因,我似乎可以抛出一个类似“后奥运时代电影格局”的概念。这个过程大概要追溯到02年《英雄》开启的中国式大片时代,此后在《无极》形成怪诞的电影文化氛围,而电影观众回归理性之后,似乎有了“春季档”的概念——比如去年的《立春》和《左右》,甚至细微到“三八档”——比如《双食记》。《二十四城记》号称也是三八档,当然这一切都与所谓“三代厂花”的剧情简介一样不靠谱。而奥运会开幕式作为08年度第一大片,实实在在地展示了中国电影文化的深刻程度——有个冷笑话叫做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电影的国家,因为中国连国歌都是电影插曲——而对奥运开幕式的评论,先批后赞,最后抓了央视当替罪羊,又成为终结华语大片时代的怪诞闹剧的标志。
我所谓“后奥运时代电影”大约伴随着院线的增加,公映影片的增加,影评作用的强化以及观众逐渐的理性观看。02年到07年的狂欢客观上也培育了进一步市场和观众,而同时伴有的则是艺术片的逐渐浮出水面,随着电影文化的发展和资源的普及,看多了各国商业片和大众艺术片的观众也能够接受国产艺术电影了,这大概是本片小小票房奇迹的原因。但是对本片批评的声音却很多。看了一些评论,好像本片有不止一个版本——至少我今天在影院看的115分钟版本里没有华润的广告,没有赵涛哭着说我就想在24城给父母买栋房子这样的台词,我猜想大概是公映版本与宣传的免费版本的不同?当然更核心的原因是,贾樟柯曾经作为一代文艺青年的必修课深入人心,而这些文艺青年未必接受这种影院的观看方式——贾樟柯的片子,应该是非主流的,被禁的,只能通过下载和盗版得到的,某种接头暗号式的存在,而如果他上了院线,就是堕落了——这大概是对一部分影评进行精神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可是不要忘了,贾樟柯根本就是一个看着港片长大的导演——而且电影说到底是要卖钱的。
现在回想起来,06年还上演过“《三峡好人》pk《黄金甲》”的喜剧,而所谓“观众”早已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但电影文化却实在短短几年间生根发芽,于是终于我们不再同一时间只有一部电影可看,于是“看什么”和“怎么看”也逐渐成了问题。当然贾樟柯的形式主义仍然在考验观众——因为对这部影片,收回成本甚至赚钱都已经不再是问题,大约说到最后,觉得影片值不会票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不是这也是批多于赞的一个原因?然而我想说的是,在与宣传完全悖离的影片面前,似乎未经训练的观众难于找到一个立场,大概这又导向了“首周舆论决定论”。
五、二十四城记
于是在只有4个人的小放映厅里,我看到了这么一部贾樟柯依然在关注流动和寻找的影片。这部影片里充满着逝去的岁月的哀伤,它关于一个厂,一座城,一个国:这座厂可以是任何一个经历了和经历着中国当代史巨变的大型国企,里面有众多渺小的人,也有众多巨大的厂房和机器,有太多的悲喜日夜上演;这座城不是任何一座城,而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城市,它在这里降落,一如《孔雀》和《立春》里的鹤阳,而这座城市终于会消失,一如《三峡好人》里的奉节,在这里,这座城变成了资本洪流之中的一栋楼盘;而这个国家,是反反复复被讲述的中国,关于历史也关于未来,关于故事里的人和我们这些听故事的人。你说历史是有意义的么?你说是不是只有故事才是历史,还是历史本来就是需要被讲述为故事?于是我们更愿意坐下来听一个故事,听那些远去的昔日荣光,听这个时代不断成长。
一、言说
贾樟柯无疑是十足自恋的,这里的自恋没有任何贬义,而是说他对自己的电影方式和自己的生命情有独钟。《二十四城记》在贾樟柯的作品序列中处在一处转折点,贾樟柯用这部影片对此前的作品做了一次有趣的总结。原谅我只能用“有趣”这个词,当然也可以说是奇妙的,因为这部片子在我的视野里,是中国电影序列里仅见的“仿纪录片”(Mock Documentary指用纪录片手法和表象拍摄的故事片。当然“纪录片”这个词本身也是裂隙纵横,至少包含了三种以上的不同影片类型,此处从略)。而这次影片又像一次长长的注目礼,对贾樟柯自己的电影作品,更是对中国当代史的后半段——于是我知道贾樟柯无论是从表达欲到叙事野心,都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部影片显然是过分表达的,因为“表达”或者“言说”甚至成了直接的表象和影片的主部。此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在大银幕上看纪录片(无论是哪种的纪录片)的经验——最多是在教室看过投影。这一次我的震惊体验大概与超级写实主义的油画类似,影院的大银幕上访谈和“访谈”的单调构图对我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而贾樟柯的策略,或者说影片结构,则是“真假参半”,用访谈和记录引入规定情境,然后再用一样的手法——被放大的“言说”——来进行叙事。试想倘若不是吕丽萍陈冲赵涛陈建斌,那么她(他)们的“扮演”行为是不是仍然能够被指认?或者,那些“受访者”同样也是在“扮演”?这里涉及到摄影机本身的权力问题,也就是说在摄影机下展示出来的是否还是“真实”,那么贾樟柯的回应则是两种——第一,有且只有言说,而言说的内容只好请观众“脑补”(脑内补完);第二,用职业演员的扮演在某种程度上提示这一“言说”的实质。换言之,我们并无必要去追究那些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当然可能有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在一本或者可能存在的《成发集团发展史》中有记载;或者也可能有一个酷似陈冲的上海姑娘——但是这些不是重要问题,重要问题在于这一切的呈现方式。
因为“言说”这一表象的存在,以及前30分钟的访谈和后75分钟的“访谈”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互文关系,有必要强调的是,“访谈”中的“故事”可能是特定场景下的故事,也可能是对生活的某种提炼。实际上除了第一个访谈,此后的访谈都具备充分而完整的故事性,它们就是故事本身,由此也再次对故事进行了自指——贾樟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如果不用这种手法,这部片子要么是一个N段式电影,要么是一个依那里图式的多线交织的后现代故事片。
于是从这个表象入手,对《二十四城记》的解读就会完全改变,因为首先重要的不是影片内容而是影片的形式——对纯形式的解读完全可以导向某种意识形态批判。当然可以把这种手法理解为缺少投资和缺乏能力——试想以这部高清数字电影的成本如何能cover一个跨越40年的史诗级别的故事?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贾樟柯的这种手法是有意为之——至少他不隐藏导演和摄影机,并且曝露了故事的讲述机制。
二、叙事
或许刚才的分析会导致对这部电影“形式大于内容”的判断。而就影片试图表达的内容而言,无疑是大大溢出了影片的范围。影片呈现的是一段历史,那么这部影片自然进入“当代史叙述”的序列中。420厂的历史,与中国当代史基本是等价的——从“以小见大”的角度来说。虽然当代史的禁区依然是禁区,比如文革(第一段访谈里的武斗),比如八九(好像与本片没有关系),但至少贾樟柯还讲到了不可绕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去年对新时期的回顾之中绝少提到的话题。当然大书特书的则是93年资本主义化进程开始之后的“分享艰难”,呈现方式则是讲述之中对“昔日荣光”的怀念和受访者无一例外的眼泪。贾樟柯最娴熟的技巧——用流行歌曲来标定时代——又一次成了他在影片中的签名,也是他一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结构当代史的方式。
受访人物的出场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建厂之初一直到现今的“80后”。一共8个受访者,其中4个演员,3个“真人”,剩下一个赵刚——大概能各算一半吧。这也是颇具形式感的安排。贾樟柯并无意通过他们的讲述构筑一个整体的叙事,但这些生命片段的交织却产生了某种蒙太奇层面上的意义。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讲述出来不过也是如此几句。在这些讲述之中,我们得知了420厂的变迁——它着实是一处“飞地”,如《世界》里的世界公园一般,超大规模的移民,一个工厂甚至成了一个小型规模的城市——有学校、电影院、游泳池,大量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人——大型国有企业的普遍处境。似乎用“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来下按语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部影片里的“工人阶级”多久没有在影片中出现了?曾经的“工人阶级专政”似乎也不再作为一个常见的提法了。而最后工厂变成楼盘,似乎也是某种当下资本取得胜利的隐喻。于是成都终于把曾经的飞地吞入肚中,荣光无限的工人阶级也光环不再,终于还是在社会巨变面前成了各谋生路的市民。
就“当代史书写”而言还可做出一篇大文章,但无论如何,贾樟柯这次展示出来的却是从《站台》一以贯之的视野,而《三峡好人》之中的潜台词——郭斌曾就职的工厂,以及作为“福建女老板”的翟永明开发的地产——在这里被详细的呈现。贾樟柯作为“70年代生人”的自觉使得他对80年代的叙述格外地精彩,附带地也造成了某种断裂和含糊,尤其表现在某种“更久远”的历史的状态下。
三、观看
贾樟柯的风格,或者说是“作者要素”,在影片中依然熟悉,比如逆光的窗户——得自侯孝贤的一种构图方式,还有很多,比如举着吊瓶的吕丽萍等等。当然非常明确的一个前文本是《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同样在处理“拆迁”这个命题,于是很多镜头都很相似,贾樟柯式或者余力为式的小横移,但由于高清本身的问题使得运动镜头不太流畅,还有最后一个俯瞰成都的镜头,明明就是《三峡好人》的情绪的延伸。于是《二十四城记》同样具有了某种史料价值,我曾在对《三峡好人》的评论中说“《三峡好人》真正所讲的故事是后工业时代中国的一个城市如何将要被废弃,如何正在一点一点消失,从而构建的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寓言。”而《二十四城记》要讲述的则是更深刻和更直接的层面上的问题——不是因为要建水电站,而是因为资本的介入;不是一个城市的消失,而是某个与红色历史相关的“飞地”的最终消失——这是否也是对红色历史的某种评判我不得而知。
然而还可引起注意的是访谈人物的选取,女人——四个女人,尤其后三个,承担了不同程度上的悲剧。如果不是毛的军工企业“靠山方针”,那么侯丽君的母亲与外婆是否不会分离十几年,是不是那么多东北人不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四川,是不是大丽丢失的孩子能够被找到,是不是顾敏华不会陷在成都和上海的夹缝之中而孑然一身?这些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但是有趣之处在于,女人们的讲述和男人们的讲述是完全不同的。除开第一位受访者何老先生,陈建斌扮演的副厂长和作为主持人的赵刚显然都是成功人士,或许是我的误读,或许也是《渴望》以来的中国情节剧苦情戏的传统使然。当然最精彩的段落是陈冲的20分钟——首先视觉上呈现为人物和人物旁边的镜像,而顾敏华和小花本身也是一组镜像,在加上陈冲这个集两个角色为一身的演员,实在是颇为精致的结构。当然导演安排陈冲观看电视中《小花》的段落,于是这就呈现出一组“历史的镜像”,影片的结构意义从而也被揭示出来:那正是处在当下的人们对历史深处自己的回望,以及注目礼——是行礼,更是送别。
放在“第六代导演”的序列里,作为核心表征的“自视”依然在这部影片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过《二十四城记》更像面对心理医生的一次访谈,结论,大概是最终的疗愈吧。
至于贾樟柯刻意不让身为易太太的陈冲打麻将,而让赵涛扮作王佳芝去香港跑单帮,只能看做是他的恶趣味……
四、贾樟柯
最后要说的则是有关“电影的事实”。贾樟柯作为新科金狮导演和法国电影界的至爱,本片入围戛纳理所应当,但是获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评委大概完全不知道这部电影在说什么。有趣的地方是本片在国内的某种程度上的悖反——评论以批居多,票房却是意外的好,上映三天过百万,虽不及某片和某片的一个零头,但终归是小贾老师的个人票房最佳了。
至于原因,我似乎可以抛出一个类似“后奥运时代电影格局”的概念。这个过程大概要追溯到02年《英雄》开启的中国式大片时代,此后在《无极》形成怪诞的电影文化氛围,而电影观众回归理性之后,似乎有了“春季档”的概念——比如去年的《立春》和《左右》,甚至细微到“三八档”——比如《双食记》。《二十四城记》号称也是三八档,当然这一切都与所谓“三代厂花”的剧情简介一样不靠谱。而奥运会开幕式作为08年度第一大片,实实在在地展示了中国电影文化的深刻程度——有个冷笑话叫做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电影的国家,因为中国连国歌都是电影插曲——而对奥运开幕式的评论,先批后赞,最后抓了央视当替罪羊,又成为终结华语大片时代的怪诞闹剧的标志。
我所谓“后奥运时代电影”大约伴随着院线的增加,公映影片的增加,影评作用的强化以及观众逐渐的理性观看。02年到07年的狂欢客观上也培育了进一步市场和观众,而同时伴有的则是艺术片的逐渐浮出水面,随着电影文化的发展和资源的普及,看多了各国商业片和大众艺术片的观众也能够接受国产艺术电影了,这大概是本片小小票房奇迹的原因。但是对本片批评的声音却很多。看了一些评论,好像本片有不止一个版本——至少我今天在影院看的115分钟版本里没有华润的广告,没有赵涛哭着说我就想在24城给父母买栋房子这样的台词,我猜想大概是公映版本与宣传的免费版本的不同?当然更核心的原因是,贾樟柯曾经作为一代文艺青年的必修课深入人心,而这些文艺青年未必接受这种影院的观看方式——贾樟柯的片子,应该是非主流的,被禁的,只能通过下载和盗版得到的,某种接头暗号式的存在,而如果他上了院线,就是堕落了——这大概是对一部分影评进行精神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可是不要忘了,贾樟柯根本就是一个看着港片长大的导演——而且电影说到底是要卖钱的。
现在回想起来,06年还上演过“《三峡好人》pk《黄金甲》”的喜剧,而所谓“观众”早已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但电影文化却实在短短几年间生根发芽,于是终于我们不再同一时间只有一部电影可看,于是“看什么”和“怎么看”也逐渐成了问题。当然贾樟柯的形式主义仍然在考验观众——因为对这部影片,收回成本甚至赚钱都已经不再是问题,大约说到最后,觉得影片值不会票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不是这也是批多于赞的一个原因?然而我想说的是,在与宣传完全悖离的影片面前,似乎未经训练的观众难于找到一个立场,大概这又导向了“首周舆论决定论”。
五、二十四城记
于是在只有4个人的小放映厅里,我看到了这么一部贾樟柯依然在关注流动和寻找的影片。这部影片里充满着逝去的岁月的哀伤,它关于一个厂,一座城,一个国:这座厂可以是任何一个经历了和经历着中国当代史巨变的大型国企,里面有众多渺小的人,也有众多巨大的厂房和机器,有太多的悲喜日夜上演;这座城不是任何一座城,而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城市,它在这里降落,一如《孔雀》和《立春》里的鹤阳,而这座城市终于会消失,一如《三峡好人》里的奉节,在这里,这座城变成了资本洪流之中的一栋楼盘;而这个国家,是反反复复被讲述的中国,关于历史也关于未来,关于故事里的人和我们这些听故事的人。你说历史是有意义的么?你说是不是只有故事才是历史,还是历史本来就是需要被讲述为故事?于是我们更愿意坐下来听一个故事,听那些远去的昔日荣光,听这个时代不断成长。
2 ) 贾樟柯:一个投机主义者
《任逍遥》之后就没看贾樟柯的片子了,当然不是因为把他把视野从山西汾阳拉到了全中国大时代,原因是我不买碟了,狂热追过所谓文艺片,狂热看过一段娱乐片。打击盗版的事业让卖碟的躲躲藏藏,我也懒得再去了,况且家里几柜的蝶也只看了六成。
好吧,说导演,说电影。
去过西藏的人回来说,西藏太商业了,我说人家也要吃饭,不能光为了你们这些观光客保留原始。
城管打人了,官员腐败了,我也说有很多是逼不得已,像邓小姐不是逼急了会杀人吗?有些城管也是被小贩骂过打过的。
那些第六代的电影在电影院公映了,我也说好啊,总比偷偷摸摸强,牺牲点自由算什么。
今天我要收回我的话,只是关于电影的我要收回。应为看了24城记这砣Bullshit。
早就觉得贾樟柯有野心,导演有野性是好事情,对于观众来说可以看到他的一部部走向大师的野心之作。但是贾不可能是,至少在我眼里他的才华已经到头了。
想反映大时代?小农村比大工厂要成功的多。小武一个人比一个厂三代人也要成功地多。一首献给爱丽丝也比幸子、早恋、下岗、拆迁这些元素成功的多。
之前网易新闻做了一个24城记的专题,一帮人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发力太狠了,B装大了,不知道杀人于无形,嚎啕大哭是不能催泪的。这些年贾樟柯都把话题放在大时代上,其实之前也是这样,但是表现形式不同。对于他对八九十年代的情感我也不怀疑,但是当你真的觉得你的表述或者你牛逼得可以让大家反思或者改变什么的时候,就误入歧途了。贾的电影注定是小武时期的影响一部分人,当他试图影集体的时候,一是他没有达登内这样的功力二或者没有他发挥功力的大环境。
三峡好人的三峡、世界的世界、24城记的改革,当描述这些时代话题的时候,作为一个阴谋论者,我只能认为贾樟柯是个投机者,就像我恶心很多媒体肆无忌惮的说512一样。也许有点夸张,但我真这样想。
推荐另外一部电影:《在屋顶上流浪 Hallam Foe》
好吧,说导演,说电影。
去过西藏的人回来说,西藏太商业了,我说人家也要吃饭,不能光为了你们这些观光客保留原始。
城管打人了,官员腐败了,我也说有很多是逼不得已,像邓小姐不是逼急了会杀人吗?有些城管也是被小贩骂过打过的。
那些第六代的电影在电影院公映了,我也说好啊,总比偷偷摸摸强,牺牲点自由算什么。
今天我要收回我的话,只是关于电影的我要收回。应为看了24城记这砣Bullshit。
早就觉得贾樟柯有野心,导演有野性是好事情,对于观众来说可以看到他的一部部走向大师的野心之作。但是贾不可能是,至少在我眼里他的才华已经到头了。
想反映大时代?小农村比大工厂要成功的多。小武一个人比一个厂三代人也要成功地多。一首献给爱丽丝也比幸子、早恋、下岗、拆迁这些元素成功的多。
之前网易新闻做了一个24城记的专题,一帮人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发力太狠了,B装大了,不知道杀人于无形,嚎啕大哭是不能催泪的。这些年贾樟柯都把话题放在大时代上,其实之前也是这样,但是表现形式不同。对于他对八九十年代的情感我也不怀疑,但是当你真的觉得你的表述或者你牛逼得可以让大家反思或者改变什么的时候,就误入歧途了。贾的电影注定是小武时期的影响一部分人,当他试图影集体的时候,一是他没有达登内这样的功力二或者没有他发挥功力的大环境。
三峡好人的三峡、世界的世界、24城记的改革,当描述这些时代话题的时候,作为一个阴谋论者,我只能认为贾樟柯是个投机者,就像我恶心很多媒体肆无忌惮的说512一样。也许有点夸张,但我真这样想。
推荐另外一部电影:《在屋顶上流浪 Hallam Foe》
3 ) 我不是怀旧,我是要记得
时代可以无视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不能无视时代。
——陈丹青
感觉最近两年,贾樟柯在内地的名望是越来越高了。原来喜欢贾樟柯的作品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主流人士”,现在贾樟柯基本上能通吃“主流人士”和“非主流人士”了。
昨天和朋友去西单,在西单图书大厦外看到好多保安和围观的人,一看那架势就知道肯定是有人正在签名售书。朋友对我说是贾樟柯在签名售书,我赶忙隔着玻璃张望一番,结果只看到黑压压一群人。后来我在着急要走的朋友的催促下,不得不走了,就这样错过了看到真人版贾樟柯的一个机会,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有一点点遗憾。
上周五晚上,去看了贾樟柯的第三部可以在内地公映的片子《二十四城记》,结果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某些情节和配乐让我流了一脸猫泪——本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事儿了,还好今天在豆瓣上的《二十四城记》页面上看到有人说“背后的小姑娘哭声很大”,还有人说“我看前大半段一直在哭”,我的心里平衡了。
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列斯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如此快速而猛烈的变化,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贾樟柯这么深刻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回想一下,在内地所有电影导演中,在过去的十几年坚持拍摄关于当下的中国的电影并且还能保证较高的艺术水准的,除了贾樟柯之外,似乎还真的就没有第二个代表性人物了。
关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其实贾樟柯本人又何尝不是“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因为就像他谈起自己为什么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决定去拍摄《小武》时所说的那样:“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无数的中国电影。我有非常不满足的地方。从这些影像里面,我们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再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真实的面貌。影像在九十年代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我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拍摄关于当下的中国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青春的选择”。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从他最新的这部作品《二十四城记》可以看出来,他依旧在坚持自己的“青春的选择”。现在的贾樟柯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记得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大概说过他是内地最赚钱的电影导演之一。虽然钱赚得越来越多了,但在创作方面,贾樟柯依旧希望自己是一个纯洁的人,他说“坚持独立性,绝不边缘化”是他做事的原则,并说他不会跟财富作对,因为他需要财富。看来兴趣和功利的交点还真就是“吉穴”,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很多中国的“艺术青年”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先努力赚钱,然后再去搞他们“最心爱的艺术”。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父母气疯,但又没有勇气去搞同性恋,他们还有搞艺术这样一条路可走。言外之意就是,搞艺术是赚不到钱的。甚至他们还会认为总是谈钱是会损害他们的“艺术气质”的,看来“艺术气质”还真就是折磨艺术业余爱好者的一种病。
说回正题,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贾樟柯,感谢他拍出了这样一部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的“伪纪录片”,这是一次迷人的尝试,通过这部“伪纪录片”,一些很普通的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这也使得他们,或者干脆就说我们吧(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的长辈也曾有过类似的欢乐和痛楚),在十年或几十年后重温这部“伪纪录片”的时候,也可以像德国艺术家安塞姆•基弗那样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我不是怀旧,我是要记得。
——陈丹青
感觉最近两年,贾樟柯在内地的名望是越来越高了。原来喜欢贾樟柯的作品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主流人士”,现在贾樟柯基本上能通吃“主流人士”和“非主流人士”了。
昨天和朋友去西单,在西单图书大厦外看到好多保安和围观的人,一看那架势就知道肯定是有人正在签名售书。朋友对我说是贾樟柯在签名售书,我赶忙隔着玻璃张望一番,结果只看到黑压压一群人。后来我在着急要走的朋友的催促下,不得不走了,就这样错过了看到真人版贾樟柯的一个机会,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有一点点遗憾。
上周五晚上,去看了贾樟柯的第三部可以在内地公映的片子《二十四城记》,结果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某些情节和配乐让我流了一脸猫泪——本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事儿了,还好今天在豆瓣上的《二十四城记》页面上看到有人说“背后的小姑娘哭声很大”,还有人说“我看前大半段一直在哭”,我的心里平衡了。
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列斯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如此快速而猛烈的变化,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贾樟柯这么深刻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回想一下,在内地所有电影导演中,在过去的十几年坚持拍摄关于当下的中国的电影并且还能保证较高的艺术水准的,除了贾樟柯之外,似乎还真的就没有第二个代表性人物了。
关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其实贾樟柯本人又何尝不是“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因为就像他谈起自己为什么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决定去拍摄《小武》时所说的那样:“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无数的中国电影。我有非常不满足的地方。从这些影像里面,我们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再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真实的面貌。影像在九十年代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我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拍摄关于当下的中国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青春的选择”。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从他最新的这部作品《二十四城记》可以看出来,他依旧在坚持自己的“青春的选择”。现在的贾樟柯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记得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大概说过他是内地最赚钱的电影导演之一。虽然钱赚得越来越多了,但在创作方面,贾樟柯依旧希望自己是一个纯洁的人,他说“坚持独立性,绝不边缘化”是他做事的原则,并说他不会跟财富作对,因为他需要财富。看来兴趣和功利的交点还真就是“吉穴”,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很多中国的“艺术青年”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先努力赚钱,然后再去搞他们“最心爱的艺术”。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父母气疯,但又没有勇气去搞同性恋,他们还有搞艺术这样一条路可走。言外之意就是,搞艺术是赚不到钱的。甚至他们还会认为总是谈钱是会损害他们的“艺术气质”的,看来“艺术气质”还真就是折磨艺术业余爱好者的一种病。
说回正题,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贾樟柯,感谢他拍出了这样一部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的“伪纪录片”,这是一次迷人的尝试,通过这部“伪纪录片”,一些很普通的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这也使得他们,或者干脆就说我们吧(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的长辈也曾有过类似的欢乐和痛楚),在十年或几十年后重温这部“伪纪录片”的时候,也可以像德国艺术家安塞姆•基弗那样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我不是怀旧,我是要记得。
4 ) 平淡,无好坏
没有完整故事的纪录片,已经很记录了。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记录,贾曾经说过,我所要描写的一种纪录片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回忆的东西。我觉得触动很多。翻新了我对于纪录的理解。这次24city,离自我的感情疏远了一些,仿佛他想说到更大众的一些东西,但是分散了。我们去电影院看的,似乎是为了纪念这样的非大众娱乐电影进入影院的一次胜利,但是上映当天的反响就很不好,大家觉得很沉闷。我看到有一些中年老年人去看,更听说在成都播放的时候很多人哭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记忆,一个城市的记忆也好,一个事件在那个年代的记忆也好,还是一群独特的身份的人的记忆,令我回想起来了。一座城市它真实的发生过这些,包含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的那些。贾樟柯的选材又一次的成功了。
首先这仍然是纪录片,纪录那些真实发生着或者发生过的事件,由于工厂太庞大了,他采用采访的形式,使这段历史和这些人们慢慢的浮现在人眼前。还是一贯的慢镜头和对景物的长长的远景描写。景物在时间的消磨中显露出它们的沧桑和情绪,这种流露常常比一段旁白或者演员的介绍更要清晰。这个工厂曾因为军械的需要一度繁盛过,甚至影响着这不同年代人的命运。第一批工人大都是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很多人一辈子也再没回去。他们之后的孩子,就在这个厂里成长,生活,甚至工作,更小的孩子的孩子,随着城市的发展,反又随同父母搬离出来,真正的使这个地方成为纪念和回忆。影片开始前我听说到的是9个故事,当然看的时候我也没真的从一数到九,采用明星演员我想他也有斟酌,只是在我看来,是比较失败的一笔。完全令小武的那种感觉消散而去。这次的主题仍然是城市进程,只是更贴近现在满城支构的城市化,播放到最后我才知道,电影名是一座楼盘的名字,楼盘在建设,它将替代大部分的工厂,替代这个年代的记忆,成为现在进行着的名词,它甚至替代了我们的记忆,当我们想起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名词是现在进行的楼盘的拔升。
我对晴说,我想起来我们家曾经有过纺织厂,麻纺厂和烟厂。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我几乎忘记了我们家出现过这些厂。他们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和这些家庭联系在一起,他们就在我身边,我和朋友的生活里。我不曾发现过原来这种联系,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转型,一些家庭的变化。虽然消失后盖起的不是24city,也盖上了一层现代化的遮盖布,令很多人忘却。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记录,贾曾经说过,我所要描写的一种纪录片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回忆的东西。我觉得触动很多。翻新了我对于纪录的理解。这次24city,离自我的感情疏远了一些,仿佛他想说到更大众的一些东西,但是分散了。我们去电影院看的,似乎是为了纪念这样的非大众娱乐电影进入影院的一次胜利,但是上映当天的反响就很不好,大家觉得很沉闷。我看到有一些中年老年人去看,更听说在成都播放的时候很多人哭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记忆,一个城市的记忆也好,一个事件在那个年代的记忆也好,还是一群独特的身份的人的记忆,令我回想起来了。一座城市它真实的发生过这些,包含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的那些。贾樟柯的选材又一次的成功了。
首先这仍然是纪录片,纪录那些真实发生着或者发生过的事件,由于工厂太庞大了,他采用采访的形式,使这段历史和这些人们慢慢的浮现在人眼前。还是一贯的慢镜头和对景物的长长的远景描写。景物在时间的消磨中显露出它们的沧桑和情绪,这种流露常常比一段旁白或者演员的介绍更要清晰。这个工厂曾因为军械的需要一度繁盛过,甚至影响着这不同年代人的命运。第一批工人大都是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很多人一辈子也再没回去。他们之后的孩子,就在这个厂里成长,生活,甚至工作,更小的孩子的孩子,随着城市的发展,反又随同父母搬离出来,真正的使这个地方成为纪念和回忆。影片开始前我听说到的是9个故事,当然看的时候我也没真的从一数到九,采用明星演员我想他也有斟酌,只是在我看来,是比较失败的一笔。完全令小武的那种感觉消散而去。这次的主题仍然是城市进程,只是更贴近现在满城支构的城市化,播放到最后我才知道,电影名是一座楼盘的名字,楼盘在建设,它将替代大部分的工厂,替代这个年代的记忆,成为现在进行着的名词,它甚至替代了我们的记忆,当我们想起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名词是现在进行的楼盘的拔升。
我对晴说,我想起来我们家曾经有过纺织厂,麻纺厂和烟厂。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我几乎忘记了我们家出现过这些厂。他们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和这些家庭联系在一起,他们就在我身边,我和朋友的生活里。我不曾发现过原来这种联系,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转型,一些家庭的变化。虽然消失后盖起的不是24city,也盖上了一层现代化的遮盖布,令很多人忘却。
5 ) 房地产商人的钞票和被侮辱与被毁灭的
华润置地应该是给了贾樟柯很大一把钞票拍《二十四城记》,作为回报,贾在片中加有售楼小姐详细地向赵刚介绍那个“二十四城”的楼盘,当她说到楼盘里保留了一部分旧厂区的标志性建筑时,我都觉得心动;扮演八二年生小女孩的赵涛(令人喷饭,她怎么也有三十好几了吧)飙着眼泪说:“我现在就是想赚钱,给我爸妈在二十四城买一套房子,我知道房子很好,但是我一定能办到……我是工人的女儿……”《二十四城记》原来是关于被侮辱与被毁灭的那些人和他们记忆……
我们之所以爱死了贾樟柯,是因为他凿实有才气,由他诠释的电影,哪怕是这么一部给地产公司做的宣传片,都冒着火花与生机……
《二十四城记》貌似原来根本就是部纪录片,八个工人弟兄正面或侧面镜头。无论是被安排的,还是剪辑使然,他们合共讲述了同一段紧凑的个人与420厂(?)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把个人史与大历史相结合是贾樟柯一直的主题,这些工人和他们与之共患难的420厂军工厂对我们来说陌生又熟悉,“这里面一定会有你自己”宣传册说,我说“或者咱爹咱妈”。
我与共同观影的蔻总都有相似的童年,那时父母都是同一个国营单位的工人或干部,我们曾经居住在几乎自成体系的单位家属大院。只是那时,我在广州、蔻总在重庆;我父母在运输公司,她父母在煤矿。我的母亲1977年被分配到广州,直到去年退休,母亲都不会讲粤语,她也根本没有必要讲,因为单位都是各地普语区来的同事,本地人很少。孩子像我和蔻总,都在单位的幼儿园、或者小学中学就读,然后慢慢地、背着某某单位的标签(tag as XXX),接触单位大院以外的世界。只是“单位”留给蔻总或我的记忆没有多少荣耀,反而多了对当时当地、以至今天仍存在的不适应,我记得不会讲方言的我被当地的小朋友排斥;对蔻总来说,还有体制改革给家庭带来的改变。蔻的父母下岗以后就开始做生意,后来他们从重庆来到北京,开始与朋友合伙做批发的生意,慢慢开起了自己家的超市,蔻总来北京读研究生,这家人至今还没有北京站住脚,比起这片土地上更多的工人与工人的孩子,我们已经是花朵……
哟贾,你又一次触到了我们心里面柔软又永远新鲜的切口,蒙灰又清新的乡愁,然而竟是在这样一个超现实的语境里……
和扮演八二年生小女孩的赵涛同样令人喷饭的还有陈冲、吕丽萍和陈建斌,以及联系讲述者的“静态镜头”。贾爱赵涛的程度可以和顾长卫恨蒋雯丽的程度相提并论,赵涛根本没有身着EXPECTION出现在此的必要(同样的《立春》里的蒋雯丽根本没有那么丑陋的必要),但是赵涛不仅来了,还讲起了重庆口音成都话、扮作一个八二年生的一个世俗女孩、在镜头前面“演讲述”。可能真实世界里的工人们实在太动人,吕丽萍和陈建斌“演的讲述”让人本能地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属于这420厂,不属于这个世界。贾导演莫名其妙的“静态镜头”(实在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人在画面里不动的镜头,我想是来自《三峡好人》中许多像景物写生一样效果的镜头,但是在这里显然是没有控制好)也到了快要引起笑场的地步,导演非常识趣地及时自嘲——我们为表敬意而强忍的笑声才得意畅快地喷发……
我可能一直会陷到这个“真实vs.虚假”的坑里爬不出来,直到陈冲地降临。我爱惨了陈冲。从《太阳照常生起》时那个爱男人爱到骨肉里的女医生起,陈冲就顶着那一朵“姣婆红”(粤语了)的光环鲜活了起来,拦都拦不住。在陈冲搔首弄姿地说“他们说我像电影(1982?年刘晓庆、陈冲、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里那个小花,从此就叫我小花了”的时候影院里竟然没有哄笑起来,想必是同场观影的人电影素质太低,没几个人了解当代中国电影(想起开映前博士姐姐坐在门口地上皱着眉说:“今天怎么没见到几个岑头的人啊”),惊喜陈冲演绎的孤独一生的厂花之余,哀悼贾把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又讲成了一个内部笑话……
不想再细数,导演如何如何通过个人史、工厂史地结合,以一个侧面重塑了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那是影片公关和戛纳评委关注的面向;这部为了纪念华润70周年的影片,硬是被贾樟柯拍成“纪念国有工厂的逝去”;冤大头华润眼看就要名利双收了,而贾为中国电影的进步又做了巨大贡献,不仅仅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导演的才华与气魄,他还活跃了市场,令投资商得到回报、树立了信心,为今后中国电影的融资建立了一个可操作的成功模型: 纪录片是不好拉投资的——虽然贾老师名气已经很大,但是房地产公司也是有常识的,知道做纪录片没名没利;贾大师用《二十四城记》重新演绎了“名导演+大明星+故事片”,告慰了几乎所有人……
仅你诓钱的一片
已经足以让中国电影荣耀一年
(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原作)
我们之所以爱死了贾樟柯,是因为他凿实有才气,由他诠释的电影,哪怕是这么一部给地产公司做的宣传片,都冒着火花与生机……
《二十四城记》貌似原来根本就是部纪录片,八个工人弟兄正面或侧面镜头。无论是被安排的,还是剪辑使然,他们合共讲述了同一段紧凑的个人与420厂(?)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把个人史与大历史相结合是贾樟柯一直的主题,这些工人和他们与之共患难的420厂军工厂对我们来说陌生又熟悉,“这里面一定会有你自己”宣传册说,我说“或者咱爹咱妈”。
我与共同观影的蔻总都有相似的童年,那时父母都是同一个国营单位的工人或干部,我们曾经居住在几乎自成体系的单位家属大院。只是那时,我在广州、蔻总在重庆;我父母在运输公司,她父母在煤矿。我的母亲1977年被分配到广州,直到去年退休,母亲都不会讲粤语,她也根本没有必要讲,因为单位都是各地普语区来的同事,本地人很少。孩子像我和蔻总,都在单位的幼儿园、或者小学中学就读,然后慢慢地、背着某某单位的标签(tag as XXX),接触单位大院以外的世界。只是“单位”留给蔻总或我的记忆没有多少荣耀,反而多了对当时当地、以至今天仍存在的不适应,我记得不会讲方言的我被当地的小朋友排斥;对蔻总来说,还有体制改革给家庭带来的改变。蔻的父母下岗以后就开始做生意,后来他们从重庆来到北京,开始与朋友合伙做批发的生意,慢慢开起了自己家的超市,蔻总来北京读研究生,这家人至今还没有北京站住脚,比起这片土地上更多的工人与工人的孩子,我们已经是花朵……
哟贾,你又一次触到了我们心里面柔软又永远新鲜的切口,蒙灰又清新的乡愁,然而竟是在这样一个超现实的语境里……
和扮演八二年生小女孩的赵涛同样令人喷饭的还有陈冲、吕丽萍和陈建斌,以及联系讲述者的“静态镜头”。贾爱赵涛的程度可以和顾长卫恨蒋雯丽的程度相提并论,赵涛根本没有身着EXPECTION出现在此的必要(同样的《立春》里的蒋雯丽根本没有那么丑陋的必要),但是赵涛不仅来了,还讲起了重庆口音成都话、扮作一个八二年生的一个世俗女孩、在镜头前面“演讲述”。可能真实世界里的工人们实在太动人,吕丽萍和陈建斌“演的讲述”让人本能地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属于这420厂,不属于这个世界。贾导演莫名其妙的“静态镜头”(实在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人在画面里不动的镜头,我想是来自《三峡好人》中许多像景物写生一样效果的镜头,但是在这里显然是没有控制好)也到了快要引起笑场的地步,导演非常识趣地及时自嘲——我们为表敬意而强忍的笑声才得意畅快地喷发……
我可能一直会陷到这个“真实vs.虚假”的坑里爬不出来,直到陈冲地降临。我爱惨了陈冲。从《太阳照常生起》时那个爱男人爱到骨肉里的女医生起,陈冲就顶着那一朵“姣婆红”(粤语了)的光环鲜活了起来,拦都拦不住。在陈冲搔首弄姿地说“他们说我像电影(1982?年刘晓庆、陈冲、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里那个小花,从此就叫我小花了”的时候影院里竟然没有哄笑起来,想必是同场观影的人电影素质太低,没几个人了解当代中国电影(想起开映前博士姐姐坐在门口地上皱着眉说:“今天怎么没见到几个岑头的人啊”),惊喜陈冲演绎的孤独一生的厂花之余,哀悼贾把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又讲成了一个内部笑话……
不想再细数,导演如何如何通过个人史、工厂史地结合,以一个侧面重塑了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那是影片公关和戛纳评委关注的面向;这部为了纪念华润70周年的影片,硬是被贾樟柯拍成“纪念国有工厂的逝去”;冤大头华润眼看就要名利双收了,而贾为中国电影的进步又做了巨大贡献,不仅仅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导演的才华与气魄,他还活跃了市场,令投资商得到回报、树立了信心,为今后中国电影的融资建立了一个可操作的成功模型: 纪录片是不好拉投资的——虽然贾老师名气已经很大,但是房地产公司也是有常识的,知道做纪录片没名没利;贾大师用《二十四城记》重新演绎了“名导演+大明星+故事片”,告慰了几乎所有人……
仅你诓钱的一片
已经足以让中国电影荣耀一年
(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原作)
6 ) 僅你消逝的一面
過去是一個倉庫,滿載著便以取用和裝配的零部件。是詹明信還是誰說過這樣一個意思。
我的過去一片朦朧。這是王小波從莫迪阿諾那裡借來贈給了小說人物王二的句子。
《二十四城記》,如同滿是零部件的造飛機工厰。走出影院二十四小時後,印象借助睡眠和現實時間而冷卻,那些在上個夜晚曡加成完整電影的零部件似乎已各自恢復其組成部分的角色,四散於頭腦信息倉庫的中心與角落。“實”訪談、“虛”訪談、穿插於人物訪談之間的半定格影像、蓮花般漂浮於各段落之上的詩句、語句、表情、微小的動作、有人聲的配樂、無人聲的配樂。另有在一切之上(或一切之下)被表述、等待被喚醒、或正在被創造的記憶,以及瑟縮銀幕數米以外座椅中、行走於暗街中、倚靠在酒館中那觀影者搖擺的自省。是,電影觀感從來也是自省。
虛實各半的訪談既是結構方法,又是否定電影(紀錄片)作為純粹真實歷史經驗(它到底存在不存在?)供給者的態度。結構實驗明示著記錄者和記憶召喚者的難以自棄身份,同時暗示著來自於過去的420厰空曠車間業已演化成龐大容器,充滿著可供消費的想象。九段訪談,由演員充任被訪者的虛構記錄輕鬆自若信息滿溢,相較之下,對原420廠工人的“實”訪談大部分時候充斥著攝影機逼視下的侷促、寡言、真偽難辨的微小肢體動作。穿插在電影各個段落的單人、兩人、家庭人物畫面或許是一百多個素材訪談的副産品,或許是特意為之,但幾乎所有非訪談人物都在鏡頭前僵硬著,如同被定格的無表情靜物。我無法確定導演意圖,但過去和從某個確定存在過的歷史時段走來並在此刻被呈現的人物,或者是被動的講述者,或者是雖然沉重但仍可操控的靜物。他們在被記錄時刻的不安似乎意味著歷史始終是語焉不詳的碎片各自墜落,若要成篇成章,只能等待著來自經驗想象的表述如輕煙一般彌漫開來。集體記憶由此有了被整合(或創造)的可能,但它難以避免地貫穿著特定歷史經驗的被動和想象編織人與記憶演繹者的主動。
電影的畫面令人焦躁,這樣的效果部分出現在影院時間,另一部分則發生在此刻對它們的零星回憶中。電影開場由主席臺望下去整齊劃一的全厰大會會場讓我難以自禁地記起瑞芬舒丹1914年驚世駭俗紀錄片The Triumph of Mind和BBC講述朝鮮大型團體操的紀錄片A State of Mind。大概是因為潛意識裡害怕追問自己的視點,這個令人不安的念頭轉瞬即逝。對於臺下人而言,這顯然是一個結束意義遠遠超出(開發商)啓程意義的會議。和如此尾音相對應的,是一度作為計劃經濟特有景觀的萬物俱全遍立全國龐大國有企業、資産和人力統一調配、大中專及高校畢業生全國範圍統一分配,以及由此被國家操控的個人與家庭命運。有趣的是,《二十四城記》中的人物(訪談對象和攝影對象)被限制在另一種統一規劃中。他們正面鏡頭,表情匱乏,個體對於歷史的反映竟如此地類同。作為個人和家庭命運操控者的國家至今面貌模糊,我們不知道它是一個空洞卻必須服從的概念,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所尋找的基於土地的情感歸屬,一種建立在理想之上的日以繼夜的想象,還是別的什麼。相對而言,要找到電影畫面、訪談形式、演員(職業演員和訪談對象)表情的操控力量來源則可能容易得多。
聲音。聲音在賈樟柯的電影裡常常猶如舞臺佈景,提示著觀衆電影所正摹擬的時代。相較低溫的畫面,《二十四城記》的聲音更加豐厚,也更加溫暖。同時,它們也是重要的懷舊元素。宋衛東(陳建斌)聊著少年時代女友和八十年代日劇《血疑》,巡夜保安腳踏車行進中途響起葉倩文的粵語歌《淺醉一生》,小花(陳沖)踩著戲服下高跟鞋以黛玉手執花籃之姿婀娜卻一臉無謂地踏出越劇《葬花》戲文,冷硬而宏大的工業史突然在文化變遷和雜糅的聲音文化産品間變得溫情脈脈起來。這或許也是《二十四城記》的矛盾所在,它無疑有著回溯歷史,至少是接近當代工業史的雄心,但到頭來卻是在歷史終結處被抽空了立足點的唏噓鄉愁。最刻意的聲音或許是一首《國際歌》合唱。坐在室內的合唱人群看來是工厰的退休工人文體活動團體,鏡頭掠過一張一張歌唱著的臉,歌聲整齊卻無力。《國際歌》對歌唱者而言,似乎是被過濾了政治意義僅餘下學習練唱用途的尋常歌曲。如此,我們確定那一整個曾經被《咱們工人有力量》無數次歌誦的高大偉岸工人階層並沒有掌控力量,他們是時代盛景追憶者但恐怕並不真正確定盛景是否當真存在過,有著堅信自己是工人孩子必成志業的後代但他們所能做的卻是不斷逃離與拋棄。就連宋衛東(陳建斌)這樣正值四字頭的昔日國企子弟,他所能提供的竟也只是孩提時代企業子弟和地方孩子疆界衝突。這些故事,也宛若盛景當年的傳奇,但卻也不無諷刺地對應著宋衛東們曾經捍衛的疆界終將在市場轉型中不復存在,而當年子弟們強行忽略地域概念的身份認同,也因此終將在他們脫離國企舊疆土回歸“地方”之後落空成虛軟乏力的懷舊。
或許是由于詩人編劇的介入,賈樟柯開始以詩句作為段落的隔斷,通告觀衆電影意圖傳達的訊息。這讓人想起王家衛放置在《花樣年華》中的密匝文字。在《二十四城記》的真實與虛構彼此越界之外,詩人(翟永明)跨了界,導演將媒介由畫面、聲音延展到文字,電影由此設了界。盡管詩解從來是開放的,但詩句的運用似乎仍然意味著我們必須了解該如何去懂得所有已經抵達的訊息。當文字現身於電影中,或許有著點睛之美,但也必須承擔起成為冗餘信息的風險。《二十四城記》中的詩句所面臨的風險遠遠大於《三峽好人》的“菸、酒、糖、茶”。
We that have done and thought,
That have thought and done,
Must ramble, and thin out
Like milk spilt on a stone.
‘Spilt Milk’, W. B. Yeats
作為觀衆,我們在銀幕上讀到的葉芝是翻譯成中文取為電影所用的葉芝。恐怕如牛奶一般潑灑在石上並非我們曾做過的、想過的,而是曾經有所為、有所思的我們,必將面對風流雨散、疏離如葭菔的結局。近兩小時的訪談,到頭來是被串聯組合的自傷身世。
整個玻璃工厰是一個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分。
——《玻璃工厰》,歐陽江河
用於《二十四城記》時,“玻璃工厰”因地制宜改為“造飛機工厰”,於是,整個造飛機工厰是一個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卻始終敵不過“他日葬儂知是誰”的黯然神傷。直至,氤氳霧氣中我們讀到:
成都,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二十四城記》近尾處四川詩人萬夏的詩句,它似乎曾經是“成都,僅你腐朽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成都的鳥瞰城貌。這句詩和這個畫面幾乎是朋友們在酒館裡爭論的導火索。《二十四城記》是否關於成都?如果是,成都是所指還是能指?如果二者皆非,那麼《二十四城記》是關於什麼?在恰逢“五 · 一二”地震之後的戛納影展,這或許並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是,“成都”是什麼?是宋衛東們曾經與之衝突的非420廠疆界的“地方”?是被挑選出來作為工業史題材載體的420廠變遷的地域載體?是早於三峽移民、早於進城務工鄉村人口的老國企跨省遷徙人生最終賴以託付鄉愁的非鄉之鄉?如此,榮耀否。整部電影,我們聽到的都是聲音,但同時,被經濟體制和國家建設規劃南北一統的衆生命運必須啞言噤聲。老國企人生似乎得到的關註最終不過是漫漶成足以令人問“偽”的懷舊,懷想之中,往事在一個曖昧不清的“成都”皆成榮耀。但除了高高在上無形貌可以描述的操控者,從興建到消失,塵揚霧散父輩自榮光且綿延至我代,誰可確定。
僅你消逝的一面,或足以讓我負累一生。
我的過去一片朦朧。這是王小波從莫迪阿諾那裡借來贈給了小說人物王二的句子。
《二十四城記》,如同滿是零部件的造飛機工厰。走出影院二十四小時後,印象借助睡眠和現實時間而冷卻,那些在上個夜晚曡加成完整電影的零部件似乎已各自恢復其組成部分的角色,四散於頭腦信息倉庫的中心與角落。“實”訪談、“虛”訪談、穿插於人物訪談之間的半定格影像、蓮花般漂浮於各段落之上的詩句、語句、表情、微小的動作、有人聲的配樂、無人聲的配樂。另有在一切之上(或一切之下)被表述、等待被喚醒、或正在被創造的記憶,以及瑟縮銀幕數米以外座椅中、行走於暗街中、倚靠在酒館中那觀影者搖擺的自省。是,電影觀感從來也是自省。
虛實各半的訪談既是結構方法,又是否定電影(紀錄片)作為純粹真實歷史經驗(它到底存在不存在?)供給者的態度。結構實驗明示著記錄者和記憶召喚者的難以自棄身份,同時暗示著來自於過去的420厰空曠車間業已演化成龐大容器,充滿著可供消費的想象。九段訪談,由演員充任被訪者的虛構記錄輕鬆自若信息滿溢,相較之下,對原420廠工人的“實”訪談大部分時候充斥著攝影機逼視下的侷促、寡言、真偽難辨的微小肢體動作。穿插在電影各個段落的單人、兩人、家庭人物畫面或許是一百多個素材訪談的副産品,或許是特意為之,但幾乎所有非訪談人物都在鏡頭前僵硬著,如同被定格的無表情靜物。我無法確定導演意圖,但過去和從某個確定存在過的歷史時段走來並在此刻被呈現的人物,或者是被動的講述者,或者是雖然沉重但仍可操控的靜物。他們在被記錄時刻的不安似乎意味著歷史始終是語焉不詳的碎片各自墜落,若要成篇成章,只能等待著來自經驗想象的表述如輕煙一般彌漫開來。集體記憶由此有了被整合(或創造)的可能,但它難以避免地貫穿著特定歷史經驗的被動和想象編織人與記憶演繹者的主動。
電影的畫面令人焦躁,這樣的效果部分出現在影院時間,另一部分則發生在此刻對它們的零星回憶中。電影開場由主席臺望下去整齊劃一的全厰大會會場讓我難以自禁地記起瑞芬舒丹1914年驚世駭俗紀錄片The Triumph of Mind和BBC講述朝鮮大型團體操的紀錄片A State of Mind。大概是因為潛意識裡害怕追問自己的視點,這個令人不安的念頭轉瞬即逝。對於臺下人而言,這顯然是一個結束意義遠遠超出(開發商)啓程意義的會議。和如此尾音相對應的,是一度作為計劃經濟特有景觀的萬物俱全遍立全國龐大國有企業、資産和人力統一調配、大中專及高校畢業生全國範圍統一分配,以及由此被國家操控的個人與家庭命運。有趣的是,《二十四城記》中的人物(訪談對象和攝影對象)被限制在另一種統一規劃中。他們正面鏡頭,表情匱乏,個體對於歷史的反映竟如此地類同。作為個人和家庭命運操控者的國家至今面貌模糊,我們不知道它是一個空洞卻必須服從的概念,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所尋找的基於土地的情感歸屬,一種建立在理想之上的日以繼夜的想象,還是別的什麼。相對而言,要找到電影畫面、訪談形式、演員(職業演員和訪談對象)表情的操控力量來源則可能容易得多。
聲音。聲音在賈樟柯的電影裡常常猶如舞臺佈景,提示著觀衆電影所正摹擬的時代。相較低溫的畫面,《二十四城記》的聲音更加豐厚,也更加溫暖。同時,它們也是重要的懷舊元素。宋衛東(陳建斌)聊著少年時代女友和八十年代日劇《血疑》,巡夜保安腳踏車行進中途響起葉倩文的粵語歌《淺醉一生》,小花(陳沖)踩著戲服下高跟鞋以黛玉手執花籃之姿婀娜卻一臉無謂地踏出越劇《葬花》戲文,冷硬而宏大的工業史突然在文化變遷和雜糅的聲音文化産品間變得溫情脈脈起來。這或許也是《二十四城記》的矛盾所在,它無疑有著回溯歷史,至少是接近當代工業史的雄心,但到頭來卻是在歷史終結處被抽空了立足點的唏噓鄉愁。最刻意的聲音或許是一首《國際歌》合唱。坐在室內的合唱人群看來是工厰的退休工人文體活動團體,鏡頭掠過一張一張歌唱著的臉,歌聲整齊卻無力。《國際歌》對歌唱者而言,似乎是被過濾了政治意義僅餘下學習練唱用途的尋常歌曲。如此,我們確定那一整個曾經被《咱們工人有力量》無數次歌誦的高大偉岸工人階層並沒有掌控力量,他們是時代盛景追憶者但恐怕並不真正確定盛景是否當真存在過,有著堅信自己是工人孩子必成志業的後代但他們所能做的卻是不斷逃離與拋棄。就連宋衛東(陳建斌)這樣正值四字頭的昔日國企子弟,他所能提供的竟也只是孩提時代企業子弟和地方孩子疆界衝突。這些故事,也宛若盛景當年的傳奇,但卻也不無諷刺地對應著宋衛東們曾經捍衛的疆界終將在市場轉型中不復存在,而當年子弟們強行忽略地域概念的身份認同,也因此終將在他們脫離國企舊疆土回歸“地方”之後落空成虛軟乏力的懷舊。
或許是由于詩人編劇的介入,賈樟柯開始以詩句作為段落的隔斷,通告觀衆電影意圖傳達的訊息。這讓人想起王家衛放置在《花樣年華》中的密匝文字。在《二十四城記》的真實與虛構彼此越界之外,詩人(翟永明)跨了界,導演將媒介由畫面、聲音延展到文字,電影由此設了界。盡管詩解從來是開放的,但詩句的運用似乎仍然意味著我們必須了解該如何去懂得所有已經抵達的訊息。當文字現身於電影中,或許有著點睛之美,但也必須承擔起成為冗餘信息的風險。《二十四城記》中的詩句所面臨的風險遠遠大於《三峽好人》的“菸、酒、糖、茶”。
We that have done and thought,
That have thought and done,
Must ramble, and thin out
Like milk spilt on a stone.
‘Spilt Milk’, W. B. Yeats
作為觀衆,我們在銀幕上讀到的葉芝是翻譯成中文取為電影所用的葉芝。恐怕如牛奶一般潑灑在石上並非我們曾做過的、想過的,而是曾經有所為、有所思的我們,必將面對風流雨散、疏離如葭菔的結局。近兩小時的訪談,到頭來是被串聯組合的自傷身世。
整個玻璃工厰是一個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分。
——《玻璃工厰》,歐陽江河
用於《二十四城記》時,“玻璃工厰”因地制宜改為“造飛機工厰”,於是,整個造飛機工厰是一個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卻始終敵不過“他日葬儂知是誰”的黯然神傷。直至,氤氳霧氣中我們讀到:
成都,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二十四城記》近尾處四川詩人萬夏的詩句,它似乎曾經是“成都,僅你腐朽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成都的鳥瞰城貌。這句詩和這個畫面幾乎是朋友們在酒館裡爭論的導火索。《二十四城記》是否關於成都?如果是,成都是所指還是能指?如果二者皆非,那麼《二十四城記》是關於什麼?在恰逢“五 · 一二”地震之後的戛納影展,這或許並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是,“成都”是什麼?是宋衛東們曾經與之衝突的非420廠疆界的“地方”?是被挑選出來作為工業史題材載體的420廠變遷的地域載體?是早於三峽移民、早於進城務工鄉村人口的老國企跨省遷徙人生最終賴以託付鄉愁的非鄉之鄉?如此,榮耀否。整部電影,我們聽到的都是聲音,但同時,被經濟體制和國家建設規劃南北一統的衆生命運必須啞言噤聲。老國企人生似乎得到的關註最終不過是漫漶成足以令人問“偽”的懷舊,懷想之中,往事在一個曖昧不清的“成都”皆成榮耀。但除了高高在上無形貌可以描述的操控者,從興建到消失,塵揚霧散父輩自榮光且綿延至我代,誰可確定。
僅你消逝的一面,或足以讓我負累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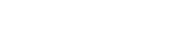




















半纪录片 总能打动人的往事 咽泪装欢
厉害 中意
不要再说“几粒职业演员坏了一锅汤”,你看他们多么卖力地不让你看出来他们是在演呀
当陈冲说出“大家都说我像小花,就陈冲演的那个”,我忍不住崩溃了,不管科长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这都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演员们都很用力,可是... meh
一个成都军工厂的衰落。纪录片与伪纪录片的结合。全片访谈式对话,访谈者贾樟柯在一半时间里对话的是真实老职工,一半是和演员扮演的老职工对话。这种手法值得品味,但也有些违和。当陈冲说起“自己长得像陈冲”,确实让人出戏。与真实人物相比,演员再精湛的表演也显得做作。三星半
二十城vs.天水围
看不懂因为你不是贫二代或者不知道这个世界有贫二代
很成都的生活
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哪个牛比人来拍南化?我提供吃住。
贾樟柯已然不再年轻,但这部电影之所以应当赢得尊重,是他选择不遗忘和讲述的诚意。中国,仅你遗忘的片段,已经足以让我无地自容。
一个疑问,为什么非要有职业演员参与?陈建斌稍好一点,只不过这个好也是侏儒比身高,没意义。最后一幕赵涛的假哭差点让我在屏幕前窒息。
“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我的子弟校童年
2009年3月2日,《二十四城记》导演见面会,散场时,送给贾樟柯一本诗集。
拍成纯粹的纪录片怎么样?
贾樟柯式怀旧,职业演员的演出都十分做作。
《东》《无用》《海上传奇》《河上的爱情》《二十四城记》没有一部能跟以前的佳作相提并论,意义何在?越来越主流的小贾令人失望。纪录片形式根本不适合他。 明星阵容也很反胃。
纪录片请换掉专业演员,太别扭了他们。
陈冲说自己长得像陈冲。。喷了